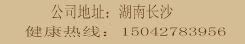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名家梁晓明随笔小品文九章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名家梁晓明随笔小品文九章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名家梁晓明随笔小品文九章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名家梁晓明随笔小品文九章
梁晓明在朗读。
小品文九章梁晓明
油画《阿尔的酒馆》,画家:文森特·梵高。
二灵酒楼
年3月,《诗刊》开大会,名曰“春天送你一首诗”,会议由宁波承办,全国四、五十诗人前往雅集。
第二日攀山,我和梁健不去,众诗人峰峦迭径摩肩接踵挥汗折枝之际,我俩却闲闲歇歇斜斜的向东钱湖边一个叫莫枝的小渔村逛去。
渔村极小,唯一的砖石小巷仅三,四人宽,青瓦房舍均不高,且旧,低矮者竟仅到人头。煤炉冒烟,渔妇摆摊,小儿露出屁股噼啪跑过,顺便就带来几缕咸咸淡淡的低迷鱼香....
再前行,忽见一基督教"房"(因在一两层民居内,不能称堂).小诧,乃入.见信徒众多,皆匝地而坐,皆举耳倾听,皆肃穆虔然.
大诧!转思今乃周日,正宗礼拜天,不觉释然。
然举目望去,见讲坛之上布道之人,身短,且粗,且壮,且黑,且丑,且满下巴胡须,然声若钟撞!滔滔不绝....
我俩洗耳细辩五分钟,一字不得——其操一口纯正当地方言也。无奈,乃出。
又思布道之人多满面胡须,暗合基督耶稣之形象,彻底释然。
返身再踏满村鱼香,不觉中午,抬眼就见“二灵酒楼”,相互一笑,我俩抬脚就进。
坐下,将以上文字发给诗友,一时回信蜂拥,言:爽快,言:哈哈,言:羡慕不已等不一而足,更有怨怪爬山辛苦以至晕倒,及称赞小文口角留香等各种角度。
我和梁健一一欣赏,看到高兴处,梁健大叫:来白酒!我虽平时不喝,但此时也气壮补充:高度的!
回想下来,实觉不虚此行也。
是为记。
年3月18日初发短信于宁波莫枝村二灵酒楼。
年1月9日补充于杭州名仕家园。
又记:
年1月20日,梁健在母亲家,下午电脑前忽然嘴鼻出血,倒地身亡。具体死因,至今未解。今年清明前三天,梁健骨灰下葬,我赶去安吉,算是见了最后一面。梁兄,现在再看这小文,当时情景历历在目,而兄却不能再在一起大叫来白酒了。生死两地,很难说你那里就不好,同样,活着的人也很难说,这里很好。一切都看自己。所以,无论哪里,我们都相互多多保重!
年4月20日记于杭州。
再记:
梁健去世一月后,下午忽得一梦,梦中有人敲门,起身开了,却见梁健呵呵笑着站在门外,我大诧!问:你不是那个什么,去了吗?他还是如平时一样呵呵笑着说:是的,来看看你。啊?我说,这也可以?
他还是那样笑着。我赶紧让进屋里,泡茶坐下,我看着他说:你等等,我到阳台看看。推开阳台,阳光灿烂,绿树游泳池均碧绿俨然。我伸出手,甚至看到阳光直接在手上明亮的晃动。这些都可以证明这不是梦境。
回到屋里,我对他说:梁健,你这可是彻底颠覆了我的人生观了!原来人死了真的可以重新归来啊。这可不得了啊!就在此时,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陆星。陆星还是那样一副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样子气息充沛的说:晓明你好!我赶紧让他进来,就坐在梁健的旁边,他俩也点头握手交谈起来,我站着恍惚看着,真觉得人生实在神奇,忽然之间,就在床上醒来。醒来觉得还在梦中.....
这之后碰到陆星,我一直不敢将这梦告知,担心一旦告知会出现什么不妙的情景。又过一年多,再次遇见,才终于忍不住告诉,陆星一笑了之,之后也没发生什么怪事。此事终于算平稳渡过。也一记。
油画《阿尔的酒馆》,画家:文森特·梵高。
罪犯、狱警和院长
大概是年,浙江作家协会主办了一次《警官三日》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三天中,早六晚九,不能回家,吃住均在监狱,应该很是辛苦,但因为组里笑话连天,更兼与什么罪犯聊天、与狱警座谈,内容甚是丰富。三天却也很快过去。时间过去了几年,今天忽然想起,信手写下这小文三篇。以做个纪念。
一:罪犯
罪犯进来了,目光闪烁,个头不高但圆头圆脑,脸色比我想象中的青菜要好的多,就象青菜它爷爷刚谈上了恋爱,苍白中竟见红润。
罪犯原为国家某部下支的一个负责人,北师大毕业,年龄不大但颇见阅历。谈吐思路清晰,逻辑分明。挪用三百万投资却如叶落风吹。水落石出,罪犯入狱。但罪犯当时不服:投资乃部门行为,罪犯却一人担当,又罪犯颇通律法,言新刑法之内,此罪本可逃脱。
我笑了,问:“即如此,你又怎成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罪犯也笑了,答:“是管教干部某某转变了他”。我诧异:“管教干部乃中专,怎改变做通你大学思想?”答:“其实也简单,挪拿别人钱财,本身是罪,新刑法此次没有,下次必有,又老天在上,我又已被捉,夫复何言?无路,唯好好改造一途”。
临别,罪犯问我何处供职,答曰:“某电视台混饭。”罪犯目光又再闪烁:“我认识杜宪(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在北京交往过......”。我又笑了:“杜宪厉害,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唯想具体地做好手边的工作,足矣。”说完我自哂地嘿嘿,他亦嘿嘿。
又几年,忽接一电话,我纳闷陌生,对面笑曰:我某某监狱的那个谁啊,减刑出狱了,来问个安好。我一惊,哦,是罪犯。转又感慨,如今全国商海翻腾,凭他机智聪明,此番出狱,就如鱼入大江,一定会有个不错的前景。也祝愿他如此了。
二:狱警
狱警名忠厚,淳安人氏。警校毕业分此当狱警。言及罪犯,狱警道:“这人聪明,几句话就明白,就怕笨的,脑子就象冬天站在石头上,水洒下去不开花,净结冰。”
狱警爱文学,听说我是作家,便问:“写小说很累的,是吗?”我笑了:“我是写诗的,不累。写小说可能是累的。”他诧异地望着我:“鲁迅不是说写诗人都是很瘦的吗?”我只好自嘲地摸摸肚子:“那都是万恶的旧社会了”。
狱警也笑:“作家都是怎么出名的呢?”我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出名的,我只知道我写出一首诗,有人看了说好,又有人看了说好,这样说来说去就传开了,后来入了作协,现在又来了这里。
狱警说你名气大吧?我说不大,小。而且写作主要是喜欢,名气对喜欢作用不大。狱警又说,我也喜欢文学。我说我知道,他很诧异。我笑了:“你一说鲁迅说诗人都是瘦的,我就知道了。做生意的,哪怕李嘉诚也未必知道鲁迅这句话”。狱警听了,很高兴。为人民服务,狱警高兴了,我便也高兴了。
狱警工作很累,早六晚九,每月休息四天。一天早上,监狱出操,我们去看,远远的操场上,雾气朦胧,一队监犯嚓嚓地前行,对首有一狱警,威武庄严,高喊口号阔步向前。雾中辩去,狱警忠厚也。我脑中忽叠印出狱警桌上的两本书,一为《爱情啊,你姓什么》,另一为《摸透罪犯的心》。
(注:忠厚聊天时说,一月休息四天,与外界联系少,故狱警结婚恋爱比较困难。)
三:院长
又一天下午,我去洗手间,门外有一清瘦文雅满头白发的男子在扫地,一见我,忽然立正大声喊道:报告!我一惊停步,赶紧回答:你好。他听了,显然一愣,嘴边微微笑了。
洗手间出来,他又停下扫帚立正。怕他再喊,我忙挥手说不要不要。走近几步,看他个不高,虽手握扫把,却感觉儒雅内敛,顿起好感,便问:你犯了什么罪?他忽然又昂头大声说:贪污!
哦,贪污。贪污还喊得这么响啊,我心里想着,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只好问一声:那你以前做什么的啊?“报告!”他又大喊一声:“某某法院院长。”
啊?法院院长啊,竟然也坐了监狱。我再看他表情庄严,身板笔直,手握扫帚,目光坚定的样子,只好说:那就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了。
“是”。他又大喊一声。
油画《阿尔的吊桥》,画家:文森特·梵高。
钓鱼冠军
杭州闲林有一钓鱼冠军,还出一钓鱼书,90年来读我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办的一个诗歌讲习班学习。不几天熟悉了,便力邀我去闲林钓鱼。
那时单身,虽对钓鱼毫无信心,但所谓闲着也是闲着,便应邀去了。
90年的闲林不同今日,山林野景一如明清,几百年变化不大可以料然。先到他家,其妻贤惠,热情上茶。"这是老公的老师",钓鱼冠军笑着介绍,我便满脸赫然,因冠军年龄胜我,又搞地质勘探,(不知为何,我对自己不懂的一切专家均自然的会生出敬意)。
饭后出发,一人一竿并一骑,乃自行车也.半小时后,见一蜿蜒小溪,三、五米宽,溪边芦苇丛生,冠军说到了,我们便翻身下车,冠军找一阴地坐下,装饵下钓。我左右张望见一地溪面稍宽阔便也兴冲冲的甩线挑标,意欲引鱼上钩,十分钟不到,冠军已三次提竿,我处却丝纹不动,又过半小时,冠军似乎不停的提竿卸鱼,我便烦燥不安,正欲起身,鱼标动了,乐极,赶紧挥竿,但兴奋过度,力量过大,眼睁睁一条手掌大鲫鱼在溪面三十公分处作了几个惊险的凌空跟斗,转身又倏忽隐入水中,那水花,简直就如中国跳水队的十米跳台。我大喊可惜,转身却见冠军往更远处走去。无奈,只好继续下竿,这样,三小时过去,夕阳斜了,冠军提着一小桶鲫鱼过来,见我脚边仅寸把小鱼两条,蹲下来耐心的嘿嘿笑了,接着,他开始指点溪涧:鱼儿们在哪里吃饭、哪里休息、哪是它们睡午觉的地方、记住,午觉与晚上睡觉又很不一样等等,你要在它们溜达的地方、甚至谈情说爱的地方下钓.....我便反击,溜达还可以,谈情说爱的地方下钩怕不妥吧?不然,他说,和人一样总爱表现,你想,你正在异性面前展示风采,忽然一道美味落在眼前,你难道不想表现一下?它一表现你就可以提钩了。说完他又嘿嘿笑着并递过一根香烟。
晚饭后告别回家,其妻提一大塑料袋过来,袋中有水,水里是冠军下午钓的二十八条手掌大的鲜活鲫鱼,我坐在公交车上,一路乘客询问买卖,我紧捏袋口,不卖!脑中便不自觉的又想起那条不知名的小溪,那些鲫鱼们散步和谈情说爱的地方……
05年4月5日又记:
此事已过去15年,时间真快,本来已几乎忘了,下午想起此事此人,忽然非常想念他,但却失了音讯,只记得姓陈,个高,脸黑,独来独往,诗歌班的其他同学都不喜欢他,不知为何,至今不解。
此刻是年8月20日,此文又过去了11年,忽然想起冠军似乎名叫:陈有为.也不知现在他在何方,而且闲林现在早已被房产彻底开发,那条小溪,估计也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世事沧桑,这也算是一个小例子了。
电影《卧虎藏龙》剧照。
大竹海守林人
浙江安吉县的大竹海是李安电影《藏龙卧虎》的景地拍摄点,那竹子漫山遍野,铺排迩来。一有风起,群山竹林喧嚣,竹浪起伏奔腾,真如绿色的大海一般。而且奇怪的是,满山翠竹,竟找不出一株树影。小时我每年经过大竹海(那时叫幽岭),都认真仔细瞪大了双眼,但就是找不出一棵树!哪怕如手指般稚嫩的树苗也杳无踪迹。
几十座山头,高高低低,左铺右展,从上到下,全是竹子!竹叶清沥,各自翻飞,而且一面青一面白,青白交替,不时变幻,气势大了,便煞是好看。
年,我与何新(其时他已在上海电视台)及梁健一起去大竹海为《中国先锋诗歌》电视专题系列片取景,拍至山腰,梁健兴起,摸出腰间金属钥匙,寻一株最粗的竹子,歪斜的刻下:“中国先锋诗歌摄制组”。梁健书法不错,但竹面硬滑,书法艺术便不得大肆舒展。
正遗憾,突从竹林土凹中跳出一破衣烂衫之中年瘦男,大喝一声:“罚款!”其时山林静寂,这一声大喊,汹汹真如虎豹之音,我等被吓,梁健更是全身一阵哆嗦,金属钥匙便脱手而出。
俄而清醒,便问为何罚款?破衣中年瘦男傲首仰天:破坏环境!损坏公物!一个字十元!
哦,明白了。中国先锋诗歌摄制组,一共九字,九十元。
但梁健抬头一看,忽然咧嘴笑了:嘿嘿,最后一个“组”字未刻。
“那八十元”。
此时情景松缓下来,而且竹林幽雅,多一人聊天岂不更美?我便上前递上香烟,没想招来更大训喝:“不能抽烟”!
我嗫嗫而退,望着他的穷寒衣衫,心中感慨:偌大竹林,山峦寂静,外无一人,他瘦小个子坚持真理,独对我等三条大汉,竟毫无惧色。真可谓"不畏强暴"之典范了。
我刚退,梁健又嘿嘿而上。你看,梁健操起了本地方言,(梁健本为安吉人),我们是老乡,能不能打点折?一个字十元太贵了。要不,一个字五元?
听梁健此言,我和何新不禁对眼诧异:知道买菜可打折,没听说罚款也可打折。这匪夷所思的念头也只有梁健能想的出来。而此时我们明白,这梁健的心情已经好了。果然他慢悠悠捡起钥匙,走上去说:你看,我们不要发票,给你五十,你可以买点老酒,你一定喝酒吧?我也是安吉人,递铺的。商量商量吧?
瘦小的执法者显然喝酒。他接过五十,再喝一声:你们算便宜的。那年新加坡人来,我罚了他们两百!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回应:一定是新加坡人不对。他们一定刻了很多字。
不对!他说,二十个。二百就是二十个字。
对,对!你一定不会多罚,很正确。
临走他再叮嘱:不能再刻了。奇怪的是梁健,竟然又赶上一步说:你看,我这个“组”字还没刻完,不完整,要不,我把这个"组"字刻掉,这个字十元。怎样?
“不行”!他大怒!
“不刻,不刻。你放心,他开玩笑的。”我赶紧补充。
他走了。望着他的小小背影越过山梁:“吾乡的人民,多么可爱,纯朴。多么坚持真理啊”。我不禁感慨。(我小学中学在安吉度过,故也自认是半个安吉人)。
黄昏下山,快离开了,梁健忽然跑开。过会回来,我问干吗去了?他说:我把那个“组”字给刻掉了。
“啊”?
(补白):何新当时拍了山腰罚款的八个字,后来又赶紧抓着梁健找到了山下那个未罚款的“组”字拍下。八个字山腰,一个字在山下,你若有机会去安吉著名的大竹海,仔细找找,一定可以看见。可惜何新现在入了佛教,这两张照片也没法找来配上了。一憾。
梁晓明在安吉老家。
有关方秉性
我读幼儿园时,父亲有天回家兴冲冲的说,我们去孝丰吧,那里山清水秀,景色优美。这样,我们就搬到了孝丰。我记得孝丰当时还有一个名称叫:丰城。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总愿意叫孝丰为丰城。现在想来一定是这个“城”字起了很大作用。到丰城不久,我们又搬到南门一个有大铁门的楼宅里。楼宅很大,有回旋楼梯,上下两层。前后门都有两个大铁环扣门。更奇特的是铁环的衔扣均为国民党旗帜的八角徽章。后听人说,此楼乃胡宗南为某姨太太所建,但未及细考。
楼宅内居住着八户人家,方秉性孤独的自住一宅。因"反动"身份,他的小屋深入黑暗,是二楼里最深的一间。印象中方秉性不言不语,进出悄悄的,几乎不发出一点声音。而他小屋的对面也住着一个有趣的人物,名字忘了,大概记得叫老苏。后来调去了林枫寺林场,好像还重新当上了一个什么领导。还邀请我们全家去林枫寺游玩一趟。老苏身材魁梧,爱拉小提琴。当时全国人民都很瘦,老苏却胖。也是奇怪。再后来有一天,父亲提着把小提琴回来,说老苏不要了,15块卖给了父亲。所以,我从小便也有了几次拉小提琴的经历。另外就是有天下午听老苏和父亲聊起方秉性,说他是个好人,是当年全国著名的中正中学的校长,经历丰富,曾被蒋介石特别表彰。因为蒋介石,我便深刻记住了方秉性这个名字。
具体时间忘了,但我永远难忘的是,有天晚上,我正站在床上跳玩,忽然看见高高瘦瘦的方秉性拄着拐杖,从我家窗前缓缓的走过。我清晰的记得我还问父亲:这么晚了,他怎么还要出去?出去干什么啊?父亲说小孩别问大人的事。当晚就这么过了。但第二天下午,小镇的乌龟头上传来消息:方秉性跳河自杀了!一想到昨晚我看见的方秉性原来正是出发前去自杀的路上,我便不寒而栗。
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生命死亡感到的寒意。这种寒意现在写来依然弥漫....
后来我还专门去看过乌龟头,乌龟头不高,大概七、八米。那小河也不深,正常时最浅仅到膝盖,但整段小河最深的就是这个乌龟头,两边狭窄,水深可过人头。一想到方秉性白天来细细的考察,仔细的挑选决定后,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再静静的滚下去自杀。心中感受真是无法用语言说清。
方秉性死后,竟至无人收尸。乌龟头上,有人用草席草草的包了他的身体,埋在何处,也无从知晓。
大约一周后,来了一四十左右的男人,乡下打扮,在方秉性的小屋整理遗物,一切都是干干净净的,(方秉性生前早已整理完毕)。他稍事打包就告辞走了。因是邻居,我亲眼目睹。
再后来听说,此人为方秉性侄儿,但具体如何,再无从知晓。
注:此文在凤凰博客贴出后,竟引来了方秉性的外孙女留言。可惜等我看到,已经是现在,六年后了。再联系已经断了。
梁晓明与汉斯布赫在德国领事馆,年。
汉斯?布赫先生要走了
汉斯?布赫要走了,时间真快,一晃,他已经在杭州待了三个月了。
三个月前,我忽然接到诗人杨炼从伦敦打来的电话,电话说,他有一朋友,叫汉斯,是德国作家,很著名,要来杭州住一段时间,他说他把我的电话给他了,到时他可能会联系我。我说,没问题。电话后半个月,我几乎已经忘了这事了,忽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说有位德国作家叫汉斯,要见我,问我有空吗?我一听,还真的来了?就这样,我们在红星大酒店有了第一次见面。
汉斯全名叫汉斯?克里斯托夫?布赫,年生,此次来杭是杭州市政府作为文化交流邀请来的,因为语言不通,翻译和接待人员又极为尊重他,说话简短而且谨慎,有时候他讲了很长,但翻译却只有一句话,我自然觉得不很对,但也没什么好说的,而有时我讲了很多,但翻译时也很短,他也觉不对,疑惑的望着翻译,但终于也这样过去了。慢慢的,终于开始讲到文学,讲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此时翻译不懂,但我一听就知道了,反而帮助翻译介绍和确定这些名字,慢慢讲开,又说了些中国的诗人和小说家,再一一对上,对上这些中外诗人和作家的名字时,感觉就像对上了密码一样,甚为开心。将近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其中讲到茶,我便说那几时我带你去看看龙井和梅家坞茶园吧,他很高兴。
慢慢交往多了,我发现汉斯?布赫极为聪明,脑子极为灵活,反应极快,而且他对中国的文化文学都有很多的了解,所以随着交往的增多,我们一起共鸣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谈的也越来越开,越来越深入。而作为翻译的研究生小张翻译起来也越来越流利,布赫便对她伸出大拇指,表扬她的翻译越来越好了。我也很高兴。晚上去泰莲坊吃饭,讲到苏东坡,没想到汉斯竟然也喜欢苏东坡,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了。于是情绪高涨,性情自然更加流畅。他讲东坡肉,我讲东坡醉酒,他讲东坡情人,我讲东坡的朝云,他讲东坡流放,我讲东坡与王安石的黄花故事,一来一往,到精彩处,便白酒啤酒相互碰撞,期间再夹杂一些东坡的著名诗句,恍然之间的那种融洽,似乎连翻译都不需要了。期间他又讲了几个他在世界各地的有趣故事,讲到日本人的仔细,海地的局势,卢旺达的独裁,当然还有中国的鲁迅和他的学生王实味(他曾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王实味的小说),言谈之间,我忽然想到这早已不是我以前概念里所认识的严肃、严谨、不苟言笑的德国人的印象了。
汉斯?布赫足迹遍布世界,他在国内不仅以作家闻名,还以公共知识分子为鲜明的特征,后来在湖畔居喝茶时,诗人阿波的夫人电影评论家苏七七对我说,他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再后来,南京的诗人,教授黄梵对我说,布赫先生曾经得过两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热情邀请他去参加南京的一个诗会。关于这个,其实我内心很想问问他,包括提名的感受。但终于到他离开,一直没有开口,因为随着交流的深入,似乎更多在文学和精神领域的纯粹共鸣,似乎连谈谈这个诺贝尔奖的提名都变得俗气了。现在想来也是奇怪。
再后来就是5月9日德国领事馆在上海专门为汉斯和我举办了一个诗歌朗诵会,领事馆还专门印了海报,诗歌册子,并把我的诗歌翻译成德文。当我拿到汉斯的诗歌时,更加觉得他的精神世界的年轻。在朗诵前,(我朗诵中文,他朗诵德文,我的六首诗,他的两首诗和一篇王实味小说的节选)。他还专门与我碰头,相互再次熟悉了解彼此的作品,并且对朗诵会的进程做了仔细的讲解,我也终于亲身领略了一次德国人的严谨和仔细。5月9日的晚会非常成功,更令人难忘的是那天其实是我的生日,之前我本想能否换个日子,但终于想到客随主便,于是就想,算了,就默默的在异乡过个悄无声息的生日吧。但是没想到,在领事馆的朗诵会刚刚结束,一位小姐端着礼品走上来,中文名叫石思平的领事跟着对大家说:今天是梁晓明先生的生日,他年生于这座城市,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在他出生的城市庆祝他的生日。在全场一片的生日歌中,我站起来,端着礼物,内心真是丰富而且复杂,不能不说话,但是那一刻真是说不出来,我只好开口说:谢谢,谢谢。领事馆翻译主管董勤文小姐走上来说,是我们老板(石思平领事)发现这个的,但是他叫我们先不说,给你个惊喜。于是我又望着这高大(我看近1.9米)、金发、微笑的领事,再次感谢:谢谢,谢谢。朗诵完,回到宾馆,布赫端着啤酒,又领着一批他的德国朋友来到我住的房间,有一位女士(小说家)竟然刚从柏林赶来,大家喝着啤酒,喜笑颜开的“胡乱”说话,所谓“胡乱”是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翻译,我不通外语,他们不通中文,人多,房间就嫌小,真是热闹非凡,不知道具体说了些什么但大家却又都非常开心,我记得我说了中文的四声发音,并演示上海,北京,杭州等的正确发声,他们很高兴,模仿着,有两位金发姑娘告诉我,她们一个在常州,一个在上海本地,特别高兴的是,临走时,她们说她们都很喜欢我的诗歌,为了表示清楚,还都一手指诗歌,一手举起了大拇指。至于为什么她们一个在常州,一个在上海,我也问了,但因语言不通,解释起来太复杂,终于还是没有明白。而布赫先生临走又专门强调:晓明,朗诵会很成功!当然这个晓明的发音还是不太准。呵呵。(三个月下来,布赫先生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中国话了,比如:不明白,没问题,没关系,无所谓等)。
5月28日,终于布赫先生要走了,我邀他再上湖畔居,他喜欢这里,喜欢这个角度远望西湖,他说他甚至自己一个人也来过这里,但是她们(指服务员)只给了他一些瓜子和花生,我听了笑了,布赫先生就是这样,虽然他今年65岁了,但孩子气甚至很重,上次朗诵会前我们碰头,他就指着我的德文诗歌说,你的诗歌是一位专家翻译的,翻得很好。我的是翻译公司翻译的,不好。我理解他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记得有一次闲谈,我说对生活我很是随便,要求不高,吃什么,穿什么,我从来不计较,但对写作和精神世界的态度,我却极为认真,不能妥协,这是我这辈子的原则和命根子。大概我说的时候很认真,布赫先生就询问翻译,得知后,他说:我也是这样的。然后伸手过来,我们便又紧紧握手。湖畔居上,看着西湖,满目碧绿的荷叶,我说布赫先生,我真是很喜欢你啊。他听了很是高兴,叫翻译对我说,他也很喜欢我,并说他在柏林有两套房子,你一定来,住我家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听了也请翻译转告:一样的,我的家,也是你的家。想到我刚买了翡翠城的房子,这样他来,也就可以单独的住一套了。也是凑巧,今天刚好是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我特别强调的给他介绍了诗人节的来历,讲了屈原整个的故事,他听得很认真,完全听明白了,特别是最后老百姓抛粽子入江,就是为了让鱼虾不要侵害屈原的身体,他表情一动,很是感动。叫翻译对我说:谢谢你的这个故事,很好。我想他以后一定不会忘了这个中国的节日了。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个悲哀的日子。5月31日,今天布赫先生将直飞柏林。祝他一路平安,此小文也算是对我们相互结识的一个纪念。
年5月31日写于杭州
诗人伊甸,图片选自网络。
老朋友伊甸
伊甸,我认他为老朋友,老兄长。他长得比我高,但高得不多,有一阵子,忽然很胖了,再过一阵子,又忽然很瘦了。我也胖,便问原因,答曰:“吃鱼肝油,效果极好,越吃越瘦,都不敢再吃了。”于是回家开吃,一瓶下去,胖了五斤。就像30岁那年,跑西湖,一个冬天跑下来,也胖了五斤。于是又不敢再吃了。自此彻底绝望:凡别人会瘦下去的办法,到我身上,必然相反。于是安静睡觉,尽量不运动,果然,不胖了。至少,保持原样了。于是开始心安,也算是找到了心安的理论。
前些天,伊甸忽然告诉我,女儿要出嫁了,希望我去。这是当然。我很高兴,但是他忽然又有些羞涩说:“本来是好事,却要你破费了。”我笑了:“这算什么啊,完全应该啊,大好事啊。”他听了,又说:“不过等你孩子结婚,刚好可以还的。”我看看他,这就是伊甸,总把事情想的极为周密,让你觉得,只要和他一起永不会吃亏,只要一起即可,连脑筋都不需要动了,因为他早就事先帮你想得周到细致了。
终于女儿出嫁了,白白的皮肤,小小的蒜鼻头,还有些张惠妹的意味。我告诉他,他回身去问老婆,老婆说,是的,也有人这么说过。他笑了,似乎从未发现自己女儿竟然和张惠妹有那么点像的意味,于是喝酒,过一会,他上台作为长辈郑重发言。当说起自己对女儿关心不够,又说女儿从此可以多爱一个人的时候,不知为何,我远远看着,总觉得他真的有些伤感。
人的思想真的混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却不能遏制的联想起了伊甸就在不久前,在另一个主席台上的发言,那是湖州沈泽宜先生去世的追悼会上,伊甸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神情自然也是庄重,言谈之间,也是极为伤感,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带着不可挽回的哀婉与悲痛。
一个逝去,一个结婚,一个彻底消散,一个重新开始。人的生命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轮回着,就在这轮回的两端,短短的时间内,伊甸就已经完成了两次最为严肃庄重的发言。
我在婚宴的坐席上,看着鹤发童颜,身材俊拔、风度极佳的伊甸满面笑容的在大厅之内来回应酬,不禁想起92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班报到的狭窄走廊上,我们相互端着脸盆行囊,面对面走过却相互高傲的直目而行,擦肩而过时,彼此连基本的招呼也不打一个。直到夜晚,因为都写诗,小小房间内,我和他竟然被分配在同一个宿舍。临床相对,黑夜深沉,终于不得不开始说话,从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直到终于越说越多,终于抛开一切创作的不同,终于,我们成了一辈子的好友。
恍惚太快,二十多年过去,除了头发变白,伊甸似乎没什么变化,而在我看来,现在的伊甸,似乎风度更加儒雅,更加魅力十足了。说了这么多,其实都不对,只有一句话想说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从认识到现在,唯一珍贵的:是老伊一点没变,说话方式,耿直大胆的态度,行事做人的细密周详,在在都令人惊讶却又忍不住心中暗举大拇指。
举例子两个:
1:大约八十年代末,在杭州黄龙宾馆对面的小山上,作协弄了个会,省里来了领导坐在上方,等领导讲完,老伊似乎第一个发言,开口就直接批判臧克家,言他发表的诗歌:“全国人民高举拳头,拳拳砸向四人帮的狗头。”老伊接着说,同样又是这个臧克家,在70年代中期,在全国大批右倾翻案风的《诗刊》第几期第几页上,又是这样写:“全国人民高举拳头,拳拳砸向邓小平的狗头。”老伊继续发言:诗歌难道就应该这样被不断的需要,而不停的高举拳头砸砸砸吗?一言落下,满场寂静!
别人我不知,但至少我当时心中凛凛冽冽的,也就彻底记下了伊甸的名字。
2:大约作家班以后,在莫干山,一次会议我和他又分配在同一个房间,也可能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了,睡前聊天,他说,男人四十岁后,就真的不一样了,他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一周一次,有时一周一次都没有,也不要紧了。那年我大概三十左右,正是精旺最好的时候,内心当然不信。但四十来临,终于有天临床不举,不禁凛然想起老伊的这句话。也可为记忆深刻。
拉杂乱写,似乎戏谑了,又似乎沉重了。其实就只是一个感慨,几十年过去,一个老朋友,始终保持不变的风骨,确实令人尊敬。(想到有些老朋友慢慢老了反而变成了以前我们年轻时不屑批判的生态,就觉得这点更加难得。)故而就随手写来。老伊,看到这文字,也不知你是否高兴。但我也不管,文责自负,谁叫我半夜睡不着,也没事干,便刚好写点字玩玩。
此刻窗外天就亮起来了。我再睡,就会心安,觉得自己终于又没有浪费,算是做了点正事了。
又记:此文当时完全是因为参加了老伊女儿婚礼后有感而写,根本没想到什么发表,也完全不去想,否则就似乎太过随意了。但其实我为文也一直随意,一认真,反而难写。但后来一次聚会,我聊起写过老伊,《文学报》陆梅女士听了说要发表,这一下麻烦了,我说我可是随意而写,没想发表的事,可能太过随意了.....但陆梅大度,说完全没问题。回后寄稿前,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给老伊先看看再定。(此前虽然写出,却一直没给老伊看过)。结果发表后,有关政治人物的一点没变(我担心这点,总觉或者不太妥当?)而有关生理的部分却被删去了。一问,竟然是老伊自己删去的。我奇怪很久,终于又遇见老伊,老伊说,政治不要紧,但这生理不好,让人家一看40多岁就有点那样,对形象不好。哈哈,老伊,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是个男人,总会有行和不行的时候,故而,我还是决定保留下来,这里发出。老伊是肯定要不高兴的,下次我赔罪。谁叫我比他年小呢?更主要我认为这个真的是没什么要紧的。完毕。
年4月1日记于翡翠城。
电影《外滩轶事》海报。
谢谢上海:看电影《外滩轶事》的一些散想
刚看完《外滩轶事》,上海,这是我出生的城市,遗憾的是,我自三岁离开再见他,却已经二十多了,人生的观念已经形成,对于自己还要生活下去的生命,以及这生命应该干什么,我早已明确。在这样早已明确的理念下,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当我晚上走在大街上,抬头看着街道两边高耸、冰冷的由大理石组砌而成的大厦,我深深感到,这是一座拒绝情感的城市,哪怕我深深怀着我是这里出生的人,我应该就是这块土地的人的情感,但是没用,记得那晚,我是多么寂寞、孤清,心中冷冷的,就那么走着,故乡,我的故乡到底是哪里?是我生长的安吉小镇?我愿意承认,但理智告诉我,那不是,那是家庭避风避雨而临时栖息的侯鸟的树枝,那树枝太小,它刚好可以承载我幼小无知的心灵和身体,一旦这身体和心灵长大,那树枝,就再也难以承重,难以成为心灵的故乡。
那么,出生地,上海,就应该是,而且可以是,并且本来就是我的故乡,但是年?是那一年吗?已经记不清了,它是那么清醒而冰冷的用大理石告诉我,你不是我的孩子,或者说,他的孩子太多了,他早已记不得我这个孩子了。于是,我的永存之地、故乡之念,便终于散开、弥漫、终至于无形.....
我已近五十,再说这些似乎幼稚,但这么说着,内心还是有些伤感,看着《外滩轶事》,看着这部几乎印象派画风的包含着人物与历史的、似乎记录又似乎故事的杂糅影片,看着片头上艺术顾问尔冬强的名字,我记得我认识他,要是没有弄错,他应该就是在上海泰康路艺术中心的主人,那年他和妻子在他的艺术中心主持举办了王寅的诗歌朗诵会,会后我们还去了他的一家书店,在那里我看到了他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合影,他说话不多,但显然对上海有极深的理解和情感,这些也都散落在他随意摆放在书店的一座钟,一本书、一本老画册,甚至一根老拐杖的身上。
其实上海,它也就隐含在这些似乎散乱、似乎随意的人物身上。就像这部电影,赫德、叶澄衷、杜月笙、周旋、李香兰....
忽然想到一段美好的记忆,那是年5月9日,当德国领事馆的领事石思平先生在他为汉斯.布赫和我专门举办的中德诗歌对话会后,他忽然送上一瓶红酒和礼物,然后面对全场听众说,今天是诗人梁晓明先生的生日,更有意思的是,他就出生在这座城市,我们祝贺他。那一刻,我几乎惊讶的说不出一句话,我是那么会说,任何场合我最不怕的,就是说话。但是那一刻,我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只记得说了,谢谢,谢谢。那是怎样的一晚?回到宾馆,布赫带着三位女士来到房间,打开啤酒,胡乱说话,真是胡乱说话,因为他们说的,我一点不懂,只记得那些女士频频竖起大拇指,胡乱说话中,弄懂了其中一位刚从柏林来,一来就参加了对话会,一参加就喜欢上我的诗歌。看着这些喜笑颜开的德国人,我觉得他们一点不像传统概念中严肃、古板,一丝不苟,他们完全就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有高兴事就高兴,有悲伤事就悲伤。
还记得他们走后,已经深夜了,我睡不着,干脆出门,又是深夜的上海,但这回却没有寂寞,内心丰丰富富的,看着那些灯红酒绿,嘴边笑笑,虽然它们与我无关,但却并没有觉得拒绝,因为那就是上海和上海人愿意过的日子。在想着《新民晚报》的记者在会后过来说,能否写篇散文给我们晚报?因为你的经历、生平以及与上海的关系,很有意思。我看着他,年纪和我差不多,我想只有这样年纪的记者才会有这样的珍惜和重视,才会注意一座城市与一个人之间隐秘的关系和意义。忽然想,难道这不就是《外滩轶事》的创作思想吗?但当时却没有想这么多,当时只管感受,最后我甚至坐到了一家街边的小吃店要了碗上海小馄饨,慢悠悠的边吃边胡乱思想着。
上海,我能不说你吗?因为母亲在这里生了我,又因为去年10月我终于陪伴着母亲重返上海,而且竟然又重新找到了她读高中的学校,以及我们居住的、那从小就如烙印一般深入我记忆的带有落地长窗的房子。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安吉一个隐藏在山里的小镇上,这落地长窗的洋房子几乎就是一个另外的世界,一个伊甸园、一个曾经怀抱着我的甜蜜梦想。当母亲看着她离开了四十五年的房子竟然依然完好,那晒过衣物的露台也依然宽敞、当她看着她读高中的学校现在变成了盐业银行,而当年就是盐业银行的这栋大楼因为老板逃往台湾,而被改装成女子高中,她却一点不知,现在老板要回来,于是这房子又变成了银行,人来人往,当我看着她手舞足蹈的告诉我的孩子,这里是她当年做体操的地方,那里又是她打羽毛球的地方,我在后面跟着,心中百般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带她来寻找?整整四十五年,离开后竟然再没回来。直到我去年问她,你还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的?她说:上海!
上海,谢谢上海。在写这些文字前,就在刚才,我还依然没有想到这点,但这样写着写着,突然又自然的冒出来:上海,谢谢。不管我是否绝望的写过:“最好我能够去国外/这样我还有家乡可以想念。”不管我是否在讲演堂上说上海完全是金钱堆砌起来的城市,每一盏灯都闪烁着黄金的光芒,你若无银子,不要进去。但是,这些都没用,一部电影,《上海轶事》,马上就把这一切清扫一空。更何况母亲在回杭州的动车上望着我,微笑说:好了,现在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人的一生,真是短暂,无论你是大家庭,还是独自一人,无论你在人声鼎沸的场所,还是深夜孤单的独对台灯,你有个地方可以追寻,有个可以寄托感受的城市和地方,那已经是为人足够的安慰和福份了。
年1月31日夜晚11点53分于杭州名仕家园
梁晓明参加诗歌活动,为孩子们签名。
我家保姆
1、我家保姆,年过五旬,受教育很少,绍兴诸暨乡下淳朴人士。
若干年前,得国家清算腐败消息,欢乐,洗衣做饭不时哼歌,连洗碗都用上了多余的力气,忽然就碰破了一只,“晃当”之声响亮,她刚恍惚,我马上告知:不破不立,就像现在的反腐,是吧?保姆一听,嫣然笑了,虽长相一般,却也露出由内而外纯朴的诸暨笑容。
过半年,见各种贪腐资金每每过亿,她大呼:太腐败了!真该打!
又过一年,有一日,忽然擦桌子时喃喃自语:这么多钱查出来,怎么也不见给我们发一点呢?我旁边听到,惊讶她的奇怪想法,但同时也思想她的想法:是啊,老百姓,衣天食地,你不发钱,她为何要为你高兴呢?
又过几月,过了中秋,见我回家,问:梁先生,你们也没发月饼?我答:反腐败,要坚决。这月饼越做越贵,不能再吃了。她一听,满脸沮丧:连我们乡下村里那么便宜的月饼也不发了……
这以后,报纸电视再有贪腐爆出的消息,她风波不起,面色宁静。
我问:阿姨怎么不关心国家大事了?她看看我:又不发钱,抓起来,不抓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闻听,指指她的脑袋:思想,思想,不要受西方势力影响啊。她下巴一倔:就是嘛。我看看她,心中暗笑,却又不禁一声长叹。
2、保姆爱干净,拖地极认真,一日我匆忙进门,一鞋踏进屋子,沙发上她看见,“腾”的一下跳起冲过来,挥手大呼:哦呦呦,我刚拖好,又被你弄脏了!我一看,果然鞋印清晰,便赶紧道歉。
保姆找来拖把再拖,口中喃喃责怪:自己家的地都不小心。我一听,不禁愣着看她:是啊,这是我家的地啊!看她拖地,我默默换鞋,弯腰刹那间,脑中一片迷茫……
3、又一晚,半夜11点多,她在客厅闭灯看电视,看得深了,不一会,黑暗中她忽然大叫:这是坏人!这是坏人,要小心啊!
我正书房看书写心得,忽然闻听,不觉吓一大跳!手一抖,一个字就写歪了……坐着想了想,便出门对她说,阿姨,明天我去买一个小的电视机,放在你房间,这样你就可以躺床上关门自在看了,你看如何?
她一听,马上说:不要不要,马上就完了,我就这里看好了,这里电视大……
年1月19日饭后闲笔一则
梁晓明在扬州。
本期编辑:若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mj/7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