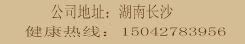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形状 > 世界石油格局重大变化下中东地缘政治研究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形状 > 世界石油格局重大变化下中东地缘政治研究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形状 > 世界石油格局重大变化下中东地缘政治研究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形状 > 世界石油格局重大变化下中东地缘政治研究
年5月2日,美国全面实施对伊朗制裁,5月14日沙特阿拉伯境内石油泵站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输送能力万桶/日的“东西横贯管道”一度关闭。中东地缘政治与国际石油博弈交织在一起,地区乱象环生,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冲击,需要对此深入研究分析,把握矛盾主线变化,判断形势并谋划应对策略。
1中东地缘政治的五种基本矛盾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主要有五种:第一,波斯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犹太民族、库尔德民族围绕地区领导权争夺、领土扩张、独立建国等诉求纵横捭阖,争斗亘古未绝;第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渊源相近,义礼颇远,伊斯兰教中逊尼派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什叶派被边缘化,宗教、教派矛盾贯穿千年;第三,中东地处五海三洲交汇之地,是世界能源供应中心,殖民时代的英法、冷战时期的美苏在此角逐,大国博弈对地区形势影响深远;第四,为复兴图强,先后兴起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主义[注释1],对各君主国、军人政府集权形成威胁,社会变革矛盾尖锐;第五,“恐怖双极”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根植于中东,恐怖主义活动波及全球,反恐斗争长期存在。
2世界石油格局变化推动形成一条新的矛盾主线二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的最初矛盾主线是犹太国家以色列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矛盾,这一矛盾经过四次中东战争和戴维营协议签署而降温。继起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与波斯民族的伊朗的矛盾,两伊鏖战八年,最终回到起点。年,美国在联合国授权下组织5国联军打赢海湾战争,并在海湾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网络,长期大规模驻军,取得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
奥巴马执政时期,在高涨的油价拉动下,美国页岩油产业蓬勃发展,加上加拿大等西半球国家的产量,已可以满足美国的需求[1]。美国对中东的石油需求锐减,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美国不再愿意在中东投入更多力量,签订伊核协议,在叙利亚战争中基本坐壁上观。
由于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中东地区大国日趋活跃。伊朗利用长达0年的和平期,加强经济和军事建设,形成了石油化工产业、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水泥业、纺织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等中东地区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海陆空三军总兵力达90万人,拥有自主研发中程导弹和潜艇的能力;年总人口达到万,成为该地区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伊朗积极扩大在中东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不断加大对各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什叶派的宣传布道、交往联络、资金援助和军事支持,逐步形成了伊朗为中心,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辐射其他什叶派居住地的什叶派势力范围[2]。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在民族、教派、政权组织形式、大国关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在地区事务主导权上构成全方位竞争关系。沙特阿拉伯的优势和短板都很明显,该国石油工业发达,年GDP值为亿美元,但工业体系不完整;军备采购金额年居世界第一,军队武器先进但战斗力低下;人口20万,但本国公民只占62%,不到伊朗的1/4;借助石油收入维持国家总体稳定,但君主制政权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面对与伊朗竞争的弱势,沙特阿拉伯站在两圣地守护者和瓦哈比思想发源地的宗教道德高地,炒作教派话题,散布“什叶派威胁论”,以此来遏制伊朗扩展地区影响[]。
尽管在全球穆斯林世界,什叶派属于少数派,但由于伊朗等什叶派国家采取鼓励生育的国策,中东人口的教派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什叶派人口接近1.亿,在西亚地区比逊尼派多出多万(见表1)。历史上饱受压抑的什叶派逐渐摆脱沉寂的状态,中东什叶派势力与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矛盾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美国、俄罗斯、卡塔尔既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方,也是世界油气大国,教派势力斗争与大国石油博弈交织,构成了当前中东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
从矛盾主线发端形成两方势力冷战时期中东划分为亲美和亲苏阵营,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亲美和反美阵营。随着地缘政治矛盾主线的转换,出于地区政治斗争的需要形成两方势力。
.1什叶派及其盟友.1.1中东地区什叶派力量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依靠人口数量优势,达瓦党等什叶派政党联盟通过选举取得了伊拉克政府的主导权,马利基、阿巴迪等多届政府均与同为什叶派的伊朗关系密切,伊朗的周边环境显著改善。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北非,所到之处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地方派系、次国家军事组织、教派团体活跃,伊朗积极介入地区各个热点,逐步将地区什叶派势力团结在周围。例如,伊朗支持巴林什叶派开展争取民主权利的持续抗议运动。年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朗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巴沙尔政权,派大批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帮助叙政府军作战。伊朗鼎力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主导的“·8”联盟,在黎巴嫩国内政坛发挥主导作用。推动黎巴嫩真主党、巴基斯坦什叶派民兵、阿富汗什叶派法蒂玛旅援助叙利亚政府军。年9月也门内战爆发,伊朗暗中向也门什叶派分支栽德派胡塞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质支援。年沙特阿拉伯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伊朗、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对沙特阿拉伯予以谴责,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什叶派新月带”自伊朗起从东向西跨越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延伸至黎巴嫩,再从北向南扩展到沙特阿拉伯、也门(见图1)。
表1年中东伊斯兰教教派人口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整理
.1.2亲穆兄会国家穆兄会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主张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伊斯兰国家治国理政与社会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反对民族主义,主张实现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伊斯兰统一。目前,穆兄会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在7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附属团体。其政治策略注重民主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积极参与议会政治,发展伊斯兰经济并向公民社会组织渗透,在中东变局后穆兄会系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利比亚“公正与建设党”等在最初选举中获胜,显示出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中东地区国家中,土耳其支持穆兄会,主要原因是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与穆兄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相似性,希望通过支持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扩大“土耳其模式”的地区影响[4]。卡塔尔看重穆兄会的国际组织和群众力量,大力提供经济支持,通过半岛电视台声援,希望影响伊斯兰主义的地区网络,将自身塑造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主义力量之间的中间人,实施“小国大外交”战略。由于穆兄会倡导泛伊斯兰合作,主张推进逊尼派与什叶派友好交流与和平对话,因此穆兄会系势力及土耳其、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友好,土耳其在卡塔尔建有军事基地。巴勒斯坦哈马斯属于穆兄会系政党,伊朗全力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卡塔尔遭遇断交危机后,得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挺过难关。
图1中东什叶派势力范围扩展
资料来源:PewResearchCenter注:图中数值为各国什叶派人口占比5%-40%
.1.俄罗斯俄罗斯积极重返中东,通过坚持联合国安理会核心地位以及国际法基本准则来重塑大国形象。俄罗斯一方面开展全方位平衡外交,另一方面对伊朗、叙利亚、真主党有所侧重。俄罗斯以中东变局为契机,以叙利亚为主要抓手,采取强硬立场,多次在联合国否决涉叙提案,联合什叶派的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在巴格达建立了反恐信息情报中心。年果断出兵与各国什叶派军事力量合作,支持叙利亚政府不断取得胜利,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国”恐怖势力。由于在美国背景的土耳其政变中,对土政府提供关键情报支持,俄土关系迅速升温。年建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方阿斯塔纳机制,进一步密切合作。土耳其因同时采购俄罗斯S-防空导弹和美国F-5战机而与美国产生矛盾后,坚持不放弃从俄罗斯采购S-,导致土美关系恶化。依托什叶派势力,拉拢亲穆兄会势力,俄罗斯成功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加了与美欧大国博弈的筹码[5](见图2)。
.2阿拉伯逊尼派及其盟友.2.1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历史上,逊尼派是伊斯兰教的主流派,什叶派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反弹。沙特阿拉伯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和欧佩克的实际盟主,又是伊斯兰教发源地,阿联酋等国希望沙特阿拉伯能够保护阿拉伯逊尼派的利益。沙特阿拉伯编织“什叶派阴谋”,将什叶派居民视为伊朗的“第五纵队”,以教派定义地区关系结构,力图阻挡伊朗影响力的南下西进。年,组织海合会出兵镇压巴林什叶派示威抗议。支持同属逊尼派的叙利亚“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和叙利亚“自由军”,提供资金、顾问、后勤援助、军事培训、先进武器。年月组织包括阿联酋、约旦、埃及、巴基斯坦、苏丹等逊尼派11国联军出兵也门,支持哈迪政府挽回败局。支持黎巴嫩逊尼派政党为主的“·14”联盟,导演黎巴嫩总理哈里里的辞职大秀,塑造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的负面形象。严厉镇压国内什叶派,年处决东方省什叶派领袖尼米尔,遭到各国什叶派抗议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宣布与伊朗断交(见图)。
图2什叶派及其盟友
尽管穆兄会也属于逊尼派,沙特阿拉伯穆兄会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对王室的合法性发起攻击。沙特阿拉伯认为伊斯兰民主政治体制如果获得成功并在阿拉伯国家推广,将对世袭制、家族制的君主王权构成挑战;而穆兄会的全球网络和在伊斯兰世界的群众基础,将影响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此外埃及穆兄会上台执政后,年2月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沙特阿拉伯认为穆尔西政府更倾向于与伊朗合作,于是联合阿联酋支持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府。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将穆兄会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由于土耳其亲穆兄会,年阿联酋天空新闻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公开支持土耳其政变;由于卡塔尔亲穆兄会,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埃及、也门等国与卡塔尔断交[6]。
图阿拉伯逊尼派及其盟友
.2.2以色列和库尔德人由于伊朗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长期支持,以色列与伊朗势不两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称为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不可或缺的盟友”。同时,以色列对推翻君主政权不感兴趣,也对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不构成威胁,沙以关系近年来迅速改善。由于以色列的科技水平和经济管理能力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海湾国家希望借助以色列实现多元化经济转型,双方合作日益密切。以色列参与了逊尼派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对叙利亚政府军、伊朗军事力量和哈马斯实施打击,客观上支援了亲沙特阿拉伯的叙利亚反对派[7]。
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由于伊拉克中央政府亲伊朗,沙特阿拉伯则暗中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武装,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以色列公开支持库尔德建国[8]。
.2.美国在中东地区大国博弈中,如果有意愿的话,美国有能力对格局塑造发挥关键影响。但是特朗普认为在中东数十年来以本土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牺牲美国士兵生命、投入数以万亿美元为代价,美国得到的回报寥寥。因此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本土至上”的孤立主义,执行“脱离接触政策”,不主张在中东地区大量投入。表现在不愿意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卷入地面冲突,年4月对叙利亚的空袭也只具象征意义,叙机场、伊朗军事基地和俄防空设施等都不在袭击范围。特朗普坦言:“美国士兵流血、出资并不能给中东带来持久和平,这里是麻烦之地;美国会尽量改善中东的安全环境,但中东问题毕竟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情;美国会向中东伙伴包括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出售武器,但不会越俎代庖。”[9]特朗普政府偏好“功能性联盟”,以拉拢沙特阿拉伯集团、扶持以色列、争取土耳其、中立伊拉克、培养库尔德人为手段,多从道义上鼓励盟友积极行动以维持美国影响力。同时,加大对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军火出口,年与沙特阿拉伯签订亿美元军售合同,帮助盟友增强国防能力。
.大国石油博弈对双方矛盾和斗争的影响由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大国石油博弈对双方联合和斗争的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石油利益博弈与地缘政治斗争可能利益一致也可能不同,势力集团的联合靠默契,合作有边界,双方斗争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余地[10]。
原油领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石油产业持续发展,年11月原油产量达到万桶/日,超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12月,美国的原油和成品油净出口量为21.1万桶/日,首次实现净出口。而欧佩克日益疲弱,原油产量全球占比已跌至7%,在国际石油贸易中欧佩克出口占比下降到58%。目前世界原油供应初步形成了美国、欧佩克、俄罗斯三足鼎立的格局,以迅猛增长的产量为基础,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助推下,美国正成为其中的佼佼者[11]。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不得不联手应对美国页岩油气的冲击,组织14个欧佩克国家和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维也纳减产协议。受大国石油博弈的影响,俄罗斯对伊朗、土耳其的支持限定在特定国家、区域,与沙特阿拉伯不构成敌对关系;由于重大石油利益冲突,沙特阿拉伯对美国不会形成依附关系。
天然气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天然气供应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的三强格局已经被改变,美国得益于页岩油气革命,年首次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年净出口天然气亿立方米。目前卡塔尔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澳大利亚、美国紧随其后。卡塔尔天然气资源主要是位于波斯湾的北方气田,与位于伊朗境内的南帕斯气田相连,合称“北方-南帕斯气田”。该气田储量超过25万亿立方米,占卡塔尔总储量的97%。年1月,卡塔尔退出欧佩克,以摆脱欧佩克的原油限产并扩张天然气产业,因而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进一步疏远,与伊朗关系进一步密切[12]。
4围绕地区热点展开三场对局上述两方势力以控制中东地区局势、取得地区事务领导权为战略目标,通过代理人战争、武装冲突等方式开展三场对决,成为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性热点。
4.1叙利亚战争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内战与反“伊斯兰国”战争交织,跌宕起伏。年属于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被击溃,俄罗斯及什叶派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全国大部分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沙特阿拉伯等支持的“解放沙姆阵线”等反对派武装及极端组织盘缩到西北的伊德利卜(Idlib)省和东南部约旦边境处,北部土耳其边境有土耳其族武装,东北部是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和“叙利亚民主军”(SDF)(见图4)。目前叙俄联军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中部哈马(Hama)地区实施围攻。由于叛军无处可逃,联军面临苦战。
土耳其将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视为头号大敌,宣布库尔德“人民保卫军”为恐怖分子,、年先后发动“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橄榄枝”行动,占领叙利亚北部阿扎兹(Azaz)、阿尔巴布(al-Bab)、阿夫林(Afrin)等城镇。美国宣布将撤出在叙利亚的名军事人员,将为土耳其进攻库尔德人进一步打开空间[1]。
历时8年的叙利亚战争进入尾声,尽管后续各方局部军事冲突和政治博弈还将继续,但基本上可以判断将以什叶派势力一方胜利告终。
4.2也门战争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Sanaa),后南下攻克亚丁(Aden),总统哈迪逃往沙特阿拉伯。年月逊尼派联军发动“果断风暴”军事行动,帮助哈迪政府恢复了对南方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胡塞武装表现出较强的实战能力,并且得到伊朗提供的军事援助,双方在塔伊兹(Taiz)、欧代因、贝达等地展开激战,战局陷入拉锯状态。目前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什叶派聚居区占全国领土的40%和人口的65%(见图5)。
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哈迪政府对也门的实际控制有限。反胡塞集团内部的矛盾加深,年1月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攻克临时首都亚丁,占领总统府及多个战略要地,升起了也门统一前的南也门国旗。“伊斯兰国”也门分支频频制造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占领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长达一年多[14]。沙特阿拉伯利用空中优势持续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展开猛烈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对也门西海岸中部荷台达港口的封锁导致救援物资无法通行,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年,由于印巴危机和苏丹政变,大量巴基斯坦和苏丹参战部队调回本国,进一步削弱了沙特阿拉伯联军的地面战斗力。战争久拖不决,使沙特阿拉伯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图4叙利亚各派势力实际控制范围
资料来源:StratforGlobalIntelligence.Anunstablefrontier[EB/OL].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ms/39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