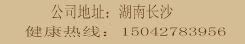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咱家有矿啊从图像与样式的角度分析三星堆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咱家有矿啊从图像与样式的角度分析三星堆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咱家有矿啊从图像与样式的角度分析三星堆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咱家有矿啊从图像与样式的角度分析三星堆
古埃及佩皮一世青铜头像,–BC,
第六王朝,开罗博物馆
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年起,延续了约年。青铜器的出现与技术的传播,可能有多种传播途径,很有可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特定部落的独有创造,因为战争,贸易,自然而然的沿着交通道路逐渐转进的方式形成是渐次传播,这属于一种常态。(比如众所周知的印度佛教东进中国),另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就是从发生地到目的地的直传,而不是逐站逐地的转进,(比如东汉明帝永平求法,派使者去印度取得《四十二章经》和佛像样式,又将取到的佛像样式雕刻在洛阳的开阳门与显节陵上,从而开启了佛像在内地雕绘的风气)。再次之外,另有一种更为有效的推行方式,即辐射式的传播,所谓辐射式,是由政治文化中心向周边的扩散推广,借助的是皇权之力,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从地缘与交通而论,陆路与海路,从哈拉帕经喜马拉雅山南麓“西南通道”,玉门关外的古代丝绸之路,海路从南海抵印度,与商文化时期最接近的主要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我们知道要开展青铜器的制造,首先需要有材料,然后要有技术。印度有丰富的铜矿和铁矿,铜矿集中在拉贾斯坦和比哈尔等地,早在公元前年就开始开发利用,这点毋庸置疑,冶炼青铜,除了需要铜以外,还需要锡,但印度本身不产锡,它冶炼青铜所需要的锡,显然是从国外输入的。印度河文明的时代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其出土的主要是母神,公牛,山羊,生殖崇拜),并没有发现大量的,成熟的批量生产的相同造型的青铜制品和金面具,而且已发掘的青铜器的造型手法与三星堆的形象没有什么重合之处。但不可否认文明相互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同外界己经有了很多联系,从楔形文字的记载和两河流域出土的物品来看,从印度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铜,木料(如柚木),石料(如闪长石,雪花石膏),奢侈品品有象牙制品,天青石,红玛瑙,珍珠以及制成的装饰品等。公元前年,印度河文明突然衰亡了,(据说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导致)。而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象牙,应该是来自古印度无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希腊语种意为“两条河之间的地方”,即指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河水带来的丰厚的沉积物形成了广阔富饶的冲积平原,这儿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摇篮,在距今上万年的石器时代,两河上游的山洞中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大约在公元前年,在下游的冲击平原上出现了最早的居民——乌博安人。继他们之后,一支名叫苏美尔的民族进入这里,承续远溯洪荒的矇昧根基,进入最初的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辉煌的文明,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议会制雏形,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距今四五千年前,已是苏美尔城邦繁荣和阿卡德帝国创立的时期,而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没有文字的史前或蛮荒状态。年至年,列奥纳德·伍利爵士对乌尔王陵的发现震惊了世人,豪华的随葬品和众多的人殉,有装饰品,武器,乐器和其他珍宝。其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金制品,包括国王用过的金器皿和金樽,以达到当时艺术的顶峰。同时,黄金打造的兵器如匕首,有的还镶嵌宝石,说明当时已有了一批杰出的金银匠人,拥有精湛的金属加工技术。(看图)重点在于,苏美尔境内没有铜矿,却在神庙里发现了几件做工极为精致的铜质艺术品。这些头像表明,艺术家已经掌握了人体的正确比例,并且,苏美尔人除了擅长用单一的金属打造物件之外,还能同时用几种金属制造工艺品。如在乌尔王陵还发现了一件小巧玲珑的神话动物雕刻,包括天青石,贝壳,蓝宝石,而那棵树,在苏美尔人的眼里则是生命的圣树。如图。更有第二代乌尔王安尼帕德建造的神庙门前的青铜匾上,刻着一只狮头鸟身的动物,这些浮雕与圆雕相结合的处理手法以及生动自然的形象塑造,反映出当时两河流域地区的青铜雕塑铸技术的惊人水平,他们对青铜铸造技术的发现早于我国夏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地区,但可惜的是苏美尔境内没有铜矿,所以,苏美尔地区并没有发现大量的,规模化制造的,形状巨大的青铜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中——商王朝的青铜礼器网络体系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中有写道:“较之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礼制的地方色彩显得更为浓郁,尤其是广汉-彭县主干交接中心的三星堆文化。”看一下考古学基于各种发现画出的商王朝的地图,展示出殷墟时期(商代晚期)商王朝的中心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北部,山西省东南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环绕这一地区的是众多的侯、伯和方国。看图。蜀人,是先秦时代部落名,也是汉族先民诸部之一。原居陕南汉中盆地及岷江上游。相传黄帝后代,蚕丛、柏灌、鱼凫代为蜀王,与夏商多交往,随周武王伐纣,封于蜀。而三星堆所处的古蜀国的位置,地理位置上远离了商文化中心。商王朝的青铜礼器网络体系繁复又有变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线索:在诸地区中,郑州—安阳地区既是原创和发射中心,同时也是接收中心;它通过以青铜器为主体的礼器来宣扬和提升商王朝的宗教,礼制和领导者的龙头地位。凝聚着神性的商式青铜礼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被塑造成与商王室所创造的聚合众神灵的普世最高集合神(可能也包括上帝)沟通的必不可少的合法媒介。当商王室无意或无力迫使所有的地区全盘接受或完全效法商王朝礼制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地诱惑那些难于控制的地区在自身礼制系统中使用商式青铜器。然而,这这些地区在如何接受和如何将商式青铜器融入其本来宗教礼仪系统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正所谓审时度势,当他们需要与最高集合神沟通或者祈求其庇护时,使用商式礼器效果最佳;而在单纯拜本地神祗或者祖先时,本地礼器既可使用,又同样行之有效。每个地区和每支文化同时保留了自己传统的神袛,各地的统治者与民众按照自己的固有礼制,通过自己的非上市礼器与地方神袛交流沟通,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独立性。由于各地区本没有商式青铜器,为了与正版商式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相一致,各地区不得不引进或模仿范样生产正宗的商式青铜礼器:在南方地区,鼎成为清江—新干地区最基本的礼器,而尊和罍则流行于城固-洋县、广汉—彭县、宁乡—岳阳、嘉山—阜南以及长江中游的江陵地区。总的来说,越接近商王朝核心区,接受礼制越彻底。远离核心区,地方特色越明显。各地区商式礼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就不足为奇了。在遥远的史前文明时代,要制造出精美,量大的青铜器是需要集体艰辛的劳动才可以的,就专家推测,铸造一件像司母戊大方鼎那样的重大多千克的青铜器,需要二百到三百人的协作,更不用说在原始的森林与矿山上去开矿,炼铜。尽管如此,中国出土的青铜器数以万计,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体型如此巨大的青铜器被制造出来呢?套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咱家有矿呀!”古代中国人掌握着超级丰富的原材料呀!江西,安徽有铜矿,锡,铅的矿藏主要在江西一带,北方地区的矿藏也不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水系发达,流通可行,不像他们的中东,希腊同行,中国的青铜工匠不曾受到原材料短缺的困扰,中国人甚至可以允许自己大量浪费金属,不去重复使用,而毫不吝啬地将其埋入地下。因为我们既掌握了技术还不缺原材料。技术高超,造型奇异,数量如此巨大的,成熟的青铜制品还展示了中国青铜器的又一显著特征:独特而复杂的铸造技术。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无非用锤揲法或失蜡法制造,中国则不然,中国古人用若干泥制阴模组成的器范铸造而成:中国人在泥制阴范中放入型芯,再将融化的调配好的铜,锡,铅汁灌入外范与型芯之间的空隙,冷却后定型就可取出,可以得到精美的饕餮花纹效果,也可以得到光滑如面的效果,都取决于泥坯的制作。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它地区都没有发明这种将设计与铸造技术融为一体的完整的体系。所以,铸造技术带来的是中国年之久的青铜时代对王权,礼仪的遵守,直至春秋战国,理乐崩坏。(陶范)
面具,最大的用途是帮助创造了一个新的祖先,或者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面具的制作,更多的是观念性的形象化,是宗教,王权崇拜的具体化。而面具中包含的许多象征性细节,比如动物特征,比如夸张成分(巨大的耳朵,突出的纵目),来源于扮演着精神力量的强大的,甚至是凶猛,危险的角色。结合人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具体表现如面部形象的处理手法上,中国的工匠熟练运用铸造法,吸取了本土文化中的抽象处理手法,五官的各部分均取大块面的造型,不做过多细节刻画,在制作泥模时采用线条加块面的处理,极度左右对称,镰刀般的眉毛,特别突出尖利笔直的鼻中线,弧线瓣状的鼻翼,并由鼻翼延伸至脸颊的浮现,去除了苏美尔人的大胡子,采用了长而直的线凸显嘴唇,一切都是为了模具化,标准化的处理,快速大量的规模化产出。历史的原因分析之后,再对三星堆的堆堆,大立人,纵目的图像学分析,在阿施怒那的阿布神庙的地窖里,完好的保存着一批圆雕人像,为我们了解早期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雕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这些公元前年——前年的作品,材料为大理石,贝壳,黑色石灰石,高近76.2厘米,外轮廓的造型非常整体,抛弃了肌肉起伏的细节处理,充分运用几何造型手法,把人体强化了圆锥,圆柱的大形体感,裙摆的细节塑造非常到位,雕像抱胸的双手与身体之间,有小小的间隙,双脚也稍稍分开。这些苏美尔雕刻艺术的传统特点:眉毛连在一起,双眼睁开很大,几乎睁裂眼眶,流露出纯真,朴实,向神祈求的目光。雕像身体绷得很直,没有丝毫动态,脸部表情划一,雕像的不同尺寸显现出社会地位的高低。如图。而金面具与青铜的结合,我们可以理解为在造型确立之后的材料上的变化,而金面具的数量,直接告诉我们,虽然冶金技术已经传到了蜀地,而黄金从古至今都是稀有产品,比铜稀有太多了。而戴上金面具的青铜器,会更尊贵,更神性。当然,这完美的冶金技术也是来自于两河文明。三星堆大立人的向前的双手,虽然线条的处理更为简练,手的大小也更为夸张,但动作的来源与两河流域汉谟拉比国王时期的一座祭祀用肖像如出一辙,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双手如握空心拳,该雕像表现的是大洪水后最后一位智者卢南那(Lu-nana)正在膜拜神明,这尊雕像由青铜和黄金制成,面部与手上有黄金,智者卢南那是单膝跪在雕刻花纹人物和文字的底座上,而三星堆的大立人则穿着雕刻花纹的衣裙站立于底座上,都戴帽,赤足,表情都严肃而神圣。大直线处理来自于阿施怒那的阿布神庙的,简约大气。关于造型上的区别与改变的理解,可以参考样式的概念,(样式,是中国美术的重要概念,用以指称具有影响一时,一地,或为后代奉为经典的范本图样,比如传自印度的造像,有佛教仪轨作为相式依据,但抑郁色彩浓厚,落地之后要经过中国的画家,雕塑家的改造绘制,将时代和民族的审美加以结合,方能与大众亲近,为百工所范,比如东晋戴逵父子改梵为夏,技术上也会因就地取材,中国古代的雕塑家除了在山体石壁上雕刻外,也发明了新的绘画的理念和方法立形塑像,比如泥胎上彩绘。在敦煌石窟中很常见。)三星堆与当时主流的商代青铜礼器同时出现蜀地,毫无疑问是与商文化完全不同的的地区性文化产物,但同时,也可以确定是形象的塑造上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的本土再创造产物。古代中国在任何时期都不是一个单元的,不是由单一文化或单一群体组成的,前仆后继直线同步发展的社会,而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政体共存,组合松懈多变,实力与影响彼此消长的社会形态,是在众多民族和众多文化相互碰撞,影响,交流与融合的漫长历程中形成的。无论是陆路与海路;无论是北线还是南线;无论西亚还是中亚;无论两河还是中国;交流,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作者简介郭彬彬年生于湖南常德。—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第三工作室,师从曹力、陈文骥,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韩国教育学博士在读。兵策儒剑补:三星堆与殷墟先后之争的简单判别术关于三星堆与殷墟谁先谁后的问题,目前争论很激烈,据说还出现了“北京派”与“四川派”。三星堆C14测年也是迷雾不断。根据《文物》杂志上个世纪刊登的有关资料表明,当时对三星堆C14测年跨度很大,从距今-年前,青铜文明主要集中时代在-年前!在有些人可能故意散布学术迷雾的情况下,我们该信谁呢?这里有一个简便的方法。本文作者说“任何一种成熟形象的出现与发展,都是有过程的,都是有迹可循的,形象与技术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本文就用面具做例子。本号在文章“三星堆面具在殷墟青铜器上的反映”里揭示了一个发现:三星堆青铜面具在殷墟并没有消失,而是集成到青铜鼎腿部了!(司母辛鼎腿上的面具纹与三星堆立体青铜面具对比)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具象到抽象”的原则,显然三星堆的面具都是一个个简单和独立具象的,而殷墟青铜鼎腿部的类似三星堆面具图案则是复杂和抽象的!那么三星堆与殷墟谁先谁后?先抛开三星堆神树和大型立人像,殷墟青铜器种类明显比三星堆多,装饰纹也更复杂,这也是从简单到复杂。即使三星堆的神树和大型人像,也可以认为是单个分离的,是简单和具象的!有没有以更抽象的形式集成到殷墟青铜器或玉器上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比如《文明起源》一书引用楚国的玉牌饰上,其上纹饰可能就是“生命之树”的抽象表达。更多参考:古埃及的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技术由来三星堆面具在殷墟青铜器上的反映国新办:承认青铜文明西来、回避炎黄华夏年文明历史的背后年时间跨度的动态古DNA信息揭示欧亚大草原路线的青铜文明传播埃夏一体论框架下的商多次迁徙考鹰蛇之夏理论框架下看三星堆文明争议背后的几个思维误区鹰蛇之夏理论框架下解读三星堆文明符号及与其他地区文明的关系欧洲人向印第安人学习“高科技”?美洲的金属文明和轮子使用鹰蛇之夏小店
鹰蛇之夏官方店淘宝店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mj/67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