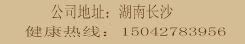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两岸视点伊核协议,或存或废蛮争触战,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两岸视点伊核协议,或存或废蛮争触战,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两岸视点伊核协议,或存或废蛮争触战,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繁衍 > 两岸视点伊核协议,或存或废蛮争触战,
本文原载于《两岸视点》年5月刊(总第58期),转载请务说明
出于对现有协议的不满,特朗普于5月8日宣布退出年签订的针对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ComprehensivePlanofAction),并决定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尽管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伊朗并没有任何违反协议、谋求核武器的行为,尽管英、法、德等国领导人的劝阻表明他们对伊朗的协议遵守状况并无不满,但特朗普仍然决定在自己设定的期限之内宣布退出。显然,此次事件关系的不仅是核武器问题,它甚至不是由核武器问题而引发。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8日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
事实上,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他们对伊核协议截然相反的态度都包含在对中东政策的整体谋划之中。特朗普宣布退出,也预示着中东新一轮变局的开端。
协议框架下伊朗的地区性扩张
奥巴马促成伊核协议的背景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美国于年底完成在伊拉克的撤军任务,奥巴马在年底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并一再削减驻阿美军数量。甚至在叙利亚战场上,美国的核心目标也从一开始的坚持推翻阿萨德政府,转变为首先消灭“伊斯兰国”。当时对于奥巴马政府,只要能够阻止伊朗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核武器,就已经是莫大的外交胜利。
在协议框架下,美、英、法、德、俄、中各国以伊朗减少离心机、限制铀浓缩活动为条件,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协议确保在年之前对伊朗核力量的管控。但是,正如特朗普及其新任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的,伊核协议没有对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施加任何限制。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伊朗利用西方各国取消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迅速增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势力。
在协议通过前的-年,伊朗的经济已经几乎陷入瘫痪。GDP在四年中有三年是负增长,石油出口从历史上的每天多万桶跌落为年的每天万桶。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后者是真正致命性的打击。但是在协议签订后的年,伊朗的GDP增长率迅速飞升至12.5%,石油出口恢复到每天万桶。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伊朗里亚尔的币值也逐渐回升。伊朗在西方的经济制裁下度过30多年,在制裁取消的那一天终于见证经济的正常发展。
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GDP增长率在年飞升至12.5%
依靠日益增强的实力,伊朗开始像解除枷锁的波斯武士一样,在中东这个角斗场上施展拳脚。美国推翻萨达姆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之后,伊拉克的什叶派执掌政权。伊朗和伊拉克都是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这为它们的战略取向提供了天然的向心力。伊朗利用帮助伊拉克打击境内“伊斯兰国”势力的机会,实现在两河流域的军事存在。年以后,伊朗仿照在叙利亚反恐的经验,与伊拉克建立一系列的军事合作和情报共享机制。年4月18日,两国国防部长在巴格达举行会谈,商议长期的国防和反恐合作事宜。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伊拉克对伊朗来说是坚不可破的壁垒。而如今,正像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伊拉克成为伊朗人向地中海沿岸扩张的通衢。
伊朗对叙利亚的支持由来已久,维持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是其地区大国战略的关键支点。在伊朗遭受“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时期,叙利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但在伊核协议签订的两个月后,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此后,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伊朗帮助叙利亚政府军逐渐收复失地。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几乎已被剿灭,政府军占据大部分国土。正是在摆脱西方的经济制裁之后,伊朗才有能力在叙利亚战场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在GDP负增长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经受这样的消耗。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五个建立什叶派政权的国家在中东形成“什叶派之弧”
打通两河流域、巩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据点,伊朗成功打造出所谓的“什叶派之弧”,再结合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也门,这些国家对逊尼派诸国形成包围之势。在这一弧形带上,作为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叙利亚是脆弱的端点,年之前的形势尤其如此。但俄罗斯的强势介入、伊朗制裁的取消,这两个伴生的因素使局势发生彻底转变。俄罗斯与什叶派三国在反恐名义下的合作,将这种联合落实在中东广袤的土地上。
当然,在这一局势形成的过程中,对伊朗制裁的取消只是动因之一,不可忽视的是俄罗斯默契的配合。由此也可见,伊核协议不仅影响中东各国的势力消长,也预示着大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
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劣势
这种转变的意义经过与年局势的对比就可以显现出来。在伊核协议签订及俄罗斯进入叙利亚之前,美国有望推翻阿萨德政权,并建立亲美的逊尼派政府。再经过消灭叙利亚及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美国可以乘势加强对伊拉克政局的掌控。这样一来,俄罗斯难以再获得插足中东事务的机会,伊朗也会被牢牢堵在内陆。
反观现在,伊朗在伊拉克派遣打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在叙利亚是阿萨德政府军的主要支持者,在黎巴嫩扶持着真主党,在也门帮助什叶派的胡塞武装组织取得政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所有由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提升伊斯兰共和国的力量和传播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局势下,首先感到威胁的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以色列和沙特。
如果说起初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恨是相互疑惧的结果,那么现在两国的对立已经因为地缘局势的演变而不可避免。在消灭“伊斯兰国”之后,谋求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扩张成为伊朗直接和首要的目标。这时,叙利亚的什叶派政权已经稳固,以色列处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南端,在地理上首当其冲,伊以之间的紧张态势迅速突显出来。伊朗早已把消灭以色列视为国家的使命,这也将是伊朗主导地区事务、成长为地区性大国必须跨越的门槛。以色列则不能容忍伊朗的军队驻扎在国门之外,如果坐视伊朗的势力沿“什叶派之弧”一天天巩固,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中海沿岸,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将不再能得到保障。
同样感到威胁的是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不会逊于伊斯兰教与其它宗教的矛盾,因为在坚持唯一教义的信徒看来,所有的他者都是异教徒。在伊斯兰国家当中,什叶派和逊尼派政权的存在对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威胁。年初,胡塞武装组织占据也门首都并成立“总统委员会”和“全国过渡委员会”,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在边境频繁交火。也门国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徒分别占到47%和53%,沙特东部的石油产区也聚居着少数什叶派,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成功给沙特国内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面对伊朗在中东的扩张,奥巴马政府一再采取守势,坚持“背后领导”(LeadingFromBehind)的政策。当时美国把伊拉克和阿富汗视为两大“赘疣”,国内普遍厌战,已经无心再向中东派遣军事力量。所以,在年伊拉克面对“伊斯兰国”的侵扰时,奥巴马拒不出兵,该国只有转向伊朗。在叙利亚战场上,美国始终只提供武器、情报和少量的协助人员,结果任由伊朗和巴沙尔政权坐大。也门陷入乱局之后,美国更是没有干预。伊核协议签订时,以色列和沙特是最激励的反对者。也由于这些因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的关系才会日益疏离。
曾有分析认为,由于页岩油的开发,美国将在年前成为能源净出口国,因此中东对于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其实,中东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美国对中东的需求,而是取决于世界对它的需求。中东仍然是亚洲和欧洲的主要石油来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扼守全球重要的航线,中东注定成为内陆和海洋大国的博弈场所。只要美国要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只要美国不得不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它就必须控制中东。
所以,美国从中东过于急切的抽身正是留给俄罗斯和伊朗的机遇。年的伊核协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俄罗斯和伊朗开始以叙利亚内战和打击“伊斯兰国”为契机紧密配合,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目前来看,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联合是针对以色列和沙特的“什叶派之弧”,也是针对美国的“俄罗斯势力之弧”。在伊朗和伊拉克军事合作的谈判中,已经屡次透露出俄罗斯的身影。如果这一弧形带能够进一步坐实,美国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效果就会更加充满讽刺。他们打垮了塔利班、基地组织、萨达姆政权和“伊斯兰国”,现在一个更强的反对势力却在原来的地域上浮现。
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与奥巴马有迥然不同的思路。奥巴马的决策背负着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一丝道德感,特朗普则决心以更加凌厉和不顾一切的姿态挽救美国的声望。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的中东
在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下,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往往借助地区国家的配合。失去叙利亚之后,特朗普在中东的反攻从以色列开始。
4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把以色列作为上任后首先访问的国家,提到对伊朗势力在中东的扩张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深表关切”。次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多达半吨的“伊朗研发核武器的材料”。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而早在这些事件之前,“伊斯兰国”甫被剿灭之际,特朗普就已经声称要把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可以说,美国在消除紧迫的安全威胁之后,抑制伊朗的势力就成为列在日程表上的下一个目标。此外,朝鲜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的和解意向也构成有利的外部因素。
有趣的是,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的军事设施发起攻击前首先访问莫斯科,于5月9日出席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式。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虽然以色列和伊朗剑拔弩张,但以色列和俄罗斯却维持着互不攻击的默契。因此,在反击伊朗的行动中,以色列显然希望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立,至少避免两国兵戎相见。5月10日,以色列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设施发起攻击,伊朗迅速予以反击。两国早期的暗地交火有演变为公开对抗的趋势。但在这种冲突的早期阶段,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
以色列国防军展示其打击的叙境内伊朗军事设施地点
什叶派诸国与以色列、沙特一派的全面对抗已经初见端倪。在以色列攻击伊朗军事设施之前的5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导弹。这些事件是两派长久对抗的近期表现,也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中东变局的开端。美国一方面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削弱伊朗的国内实力,另一方面借助以色列和沙特反击伊朗在叙利亚、也门的据点。其目标也许可表述为,使伊朗重回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前的状态,将其势力封锁在内陆。如此一来,美国才能夺回伊拉克战争的果实,其在中东掌控全局的地位也才能得到维持。
所以,在围绕伊核协议展开的一系列问题当中,伊朗是否谋求核武器并不是核心。它固然是不可忽视的量变因素,但中东的地缘政治大局已经由美国及其领导的以色列、沙特诸国与伊朗领导的什叶派诸国及其背后的俄罗斯决定。中东是大国地缘政治斗争的“破碎地带”,在这片土地上浮现的任何议题都与地区局势的演变息息相关。
西欧各国还在试图拯救伊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示愿与英、法、德、俄、中诸国协商。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协议被废弃,伊朗的选择和中东局势的演变都将再次脱离掌控,无论下次实现稳定是何种态势,其过程都必将充满惊慌、恐惧和伤痛。鲁哈尼是否能稳住国内的激进派?西欧各国能否在美国制裁下为伊朗争取经济生存的空间?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又将面临何等程度的军事压力?这些因素将决定伊朗是否会走上寻求核武器的道路,而使中东陷入核竞赛的阴云之中。一旦伊朗重启研发核武器的进程,西欧各国的立场也会随之反转。
但无论核武器这一变量的走向如何,近期的中东至少有两点可以确定:一、叙利亚的形势不会很快稳定,以色列和伊朗、甚而它们背后的美国和俄罗斯,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展开新一轮的角逐;二、伊拉克的方向仍然存在变数,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一举夺魁的什叶派领袖萨德尔宣布反对外来干涉,然而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并不会减弱美国和伊朗对该国的争夺拉拢。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mj/22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