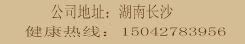纯真博物馆
皇帝回来了,排队挤在游客身后,逐一巡览他年幼时曾经居停的每一座殿堂和房间,面带暧昧的微笑,聆听导览员的讲解。历历在目的往事,成了其他人口中不尽详实的故事。
这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故事,或者说是故事的动机。所以不论是李翰祥还是贝托鲁奇,在他们拍摄末代皇帝溥仪生平的时候,都忍不住要重新演绎这一段传说中的插曲。几乎就在这两位导演构思他们的电影的同时,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也见到了已经80多岁的奥图曼帝国末代王子阿里·瓦希布(AliVasib)。王子那时候终于回到了土耳其,手上拿的却是游客签证,所以很想在找一个工作,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然后终老故土。由于他常年流亡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担任一座败落博物馆的馆长,所以饭桌上便有宾客建议,他何不干脆去当年自己住过的担任讲解员呢?王子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便开始和宾客想像,他要是真当上了厄赫拉莫尔宫导游,会怎么样和游客介绍自己曾经学习和休息的房间。帕穆克写道:「我记得后来以一个年轻小说家寻找新视角的热情来构建这些画面:『这里,先生们,』王子以他一贯的极其客气的语调说道,『是七十年前我在随从武官陪同下学数学的地方!』然后他会从那些手持门票的人群身边走开,跨过那条不允许游客跨越的线(由悬挂在黄铜立架之间的老式绒线标记,就像在我的博物馆的顶层一样),再一次坐在他年轻时坐过的桌子边。他将用同样的铅笔、直尺、橡皮、书本,演示自己在过去是如何学习的;坐在桌边,他还会向那些博物馆参观者解释:最尊贵的客人们,我过去就是这么学数学的。」
一年之后,王子就在亚历山大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始终没有达成的心愿却启发了帕慕克的灵感,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纯真博物馆》。帕慕克回忆:「脑海中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第一次想像同时成为博物馆导游和藏品之一的快乐,就像凯末尔那样;以及向游客讲解一个已经故去多年的人的一生的激动——用他在世时用过的所有私人物品。这是纯真博物馆的第一颗种子,同时作为一部小说——小说主人公凯末尔经历了同样的快乐——和一个地方。从一开始,我就同时孕育了写一部小说和建立一个博物馆的想法。」是的,《纯真博物馆》既是一部小说,也是一座真实的博物馆,叙事同时在两个面向作用,分别以文字和物件的展布追忆那一去不返的纯真年代。这座博物馆就和小说一样,里头陈示的东西都是真的,全是帕慕克自己多年来从旧货市场和古董商那里搜罗回来的物件,但构成其展示原理的逻辑则是虚构,是帕慕克这本小说里的故事。比如说一套茶具,解说词介绍那是小说主人公用过的东西。这套茶具百分百来自小说设定的年代背景,然而,小说中出现的角色就只不过是那个年代曾经活过的人群的暗影和幽灵,唯独身为灵媒的小说作家才能够呼唤出他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记忆并不可靠;但利用真实存在的材料,去虚构一段记忆,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虚构记忆,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力和情绪。这不一定是恶意(比如说复仇的意志,以及把自己变成无辜受害者的需要),相反的,它可能十分美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怀旧,通常被我们怀念的过去(所谓『黄金年代』),若不是根本不曾存在,就是被人过度渲染,甚至连最沉迷往昔的人都有可能暗自知道这一点事实。不过我们依然怀旧,因为我们对现实都不太满意,总觉得该有另一种更好的可能性。而那个更好的世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它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所以它不是一种乌托邦般的幻想,而是一种现实,只不过接下来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延续罢了。所以怀旧一方面指向的其实是未来,另一面则是坚守过往未曾完全实现的许诺。怀旧连接起了虚幻的过去和未来,即便它再荒诞也好,也总算是给了我们一种身份和历史上绵延不绝,藕断丝连的保证。人类非常需要这种历史感,它是我们稳当存活在现世的基础,让我们觉得自己脚踏实地。
清朝和奥图曼帝国都曾恶名昭著,前者号称「亚洲病夫」,后者则是「欧洲病夫」。但换上另一副眼镜,很多人有时候却觉得它们的年代其实也算盛世,于是开始追忆这两座巨大帝国的黄金年代。为什么?根据最传统的政治学定义,帝国必然是一种多民族、多文化、宗教也一样多元的政体。对比起今日中国和土耳其,甚至整个世界的那种越来越靠向单一民族主义,越来越信靠某种狭隘认同,排斥其他身份的倾向,帝国起码显得比较宽容。就拿那两位末代王孙曾经居住过的宫殿来说,没错,它们过去确实是王族的私产,但里面的收藏千奇百怪,无所不包,覆盖的范围不单来自整片帝国的辖土,更有不少异域的珍宝。它显示的既是帝国的宏大,同时也是一种对外界的好奇。如果用今天的套话来讲,形容这些故宫所改建的博物馆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的话,该怎样从那里面的物件去述说我们当下对这个民族的认知呢?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头那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的遗迹,以及用蒙文和满文铭刻的碑石,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能够把它们和自己的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吗?
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位处一条叫作「?ukurcuma」的街道。经过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繁荣,伊斯坦堡这片区域现在是一块很时尚的地方,有许多古董商,也有新派的画廊、酒吧和咖啡馆。但这条街附近却曾是有名的贫困地区,布满了日久失修的老房子,街上坑坑洼洼。在上世纪50年代,以针对外族人为目标的「伊斯坦堡暴动」以前,住在这片区域的,是一些希腊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被「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这种口号,以及无日无之的骚扰与破坏吓跑了,纷纷奔逃,留下一大片空洞的楼房,原本生机兴旺的街区这才成了贫民窟。
这些外国人的祖先原本都是帝国的臣民,其中最有趣的是「西班牙犹太人」(SephardicJews)。年,天主教王国「重新征服」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宗教迫害随之而来。原来在穆斯林王国统治下,生活还算安稳的犹太人被逼大批逃亡。当年的奥图曼帝国正当全盛,苏丹展开双臂拥抱这些拥有知识和营商经验的犹太难民,欢迎他们来到帝国的首都落户。一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只是暂住,不晓得这一住就是五百年。帕慕克后来回忆,有些犹太老人家手上居然还留存着当年西班牙格拉纳达老家的钥匙,相信自己有一天回去的时候会用得着。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之二永远的安达鲁斯如果帕慕克的记忆正确,到了20世纪上半叶,伊斯坦堡的一些残存犹太居民仍然在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当年格拉纳达老房子的钥匙的话,那么哪些当年被迫离开安达鲁斯的穆斯林又该怎么办呢?据说直到今天,特别是在北非,每当有人说起安达鲁斯(Al-Andalus)这个名字的时候,它的声音就会在空中构筑出一片有柱廊回绕的大理石中庭,阳光下一座喷泉流水淙淙。安达鲁斯,一段失落的黄金时代,一座山丘上粉红色的宫殿,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老家,是伊斯兰世界里面总能唤起些许甜美而悲哀回忆的传说。
甚至对很多现代基督徒,乃至于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达鲁斯也是一个值得追忆的对象。因为在这个世俗化的年代,一个人们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谨遵圣训的虔敬信徒。而传闻中的安达鲁斯正是那样的一个地方,虽然是个穆斯林王国,但是各种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宽容的对待,犹太教徒可以当上宰相。知识和智慧受到尊重,学者们能够任意查阅来自各种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时创发可能会背离正统的崭新思想。文化与艺术蓬勃发展,阿拉伯建筑中极尽曲折缭绕的线条在这里达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则在此时种下。繁盛的城市,喧哗的街道,总有人兜售来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总有人夜半饮酒寻欢,相信真主的宽大多于诫条。甚至连同性性行为,都在宫廷中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甜美禁果,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犹太神学最伟大的导师,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拉伯传人(那时候,亚里士多德在西欧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入读当时全欧洲规模最大的大学,后来回去还当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鲁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在学术界里面仍然引起争议。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那样的时代是真的存在过。因为它也许能够证明,穆斯林有另一种选择,甚至整个世界都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不一定要狂热拥抱某种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拥抱某种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世界本是一座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花园。
所以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达鲁斯最后而且最辉煌的据点格拉纳达沦陷,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阿罕布拉宫易主,挂上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旗帜。那时候的西班牙人简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产狂热分子,用圣战的态度来争夺领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后来甚至还向全欧洲输出令人闻风丧胆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这一年前后,「非洲人莱昂」(LeoAfricanus)诞生了,被迫从婴儿时期就开始踏上他终身不断的旅程。「非洲人莱昂」是个伟大的旅行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畅销书作者,在罗马冠上过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国宫廷。但他原本也是一个安达鲁斯人,对他而言,格拉纳达这个故乡,大概就像香港之于今天九七后才出生的年轻人,是流亡他乡(或者移民)的父亲坐在躺椅上发呆,口中呢喃的一个名词;是母亲夜半饮泣,低声诉说的一则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见闻,可惜这里头并不包括安达鲁斯和格拉纳达。这种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间,诱发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去把它填满的冲动。
阿敏.马卢夫(Amin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长在当年非常国际化的贝鲁特,母亲是拥有土耳其血统的埃及天主教徒,父亲是来自希腊的东正教信徒。黎巴嫩内战之后,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写作,不止获得了「巩古尔奖」,最后还当上了法国学术院院士。年,他第一部小说《非洲人莱昂》一出版,便立刻为他带来全球文坛的赞赏。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诗意盎然的小说就像一张魔毯,能够带领读者穿过家中衣橱的后壁,进入一个我们不曾听闻过的世界。这会不会是因为以他的背景,他特别能够体会「非洲人莱昂」旅程的意义,以及格拉纳达和安达鲁斯的价值呢?
在小说的一开头,他就用「非洲人莱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后「安达鲁斯」这个象征的启示:
「我,称重员穆罕默德的儿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约翰.莱昂。为我执行割礼的是一个剃须匠,而施洗的却是教皇。人们叫我非洲人莱昂,然而我并非从非洲而来,也不是欧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岛。人们叫我格拉纳达人、菲斯人、札亚持人,但是我并不来自任何一个国家,也不来自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里的商队才是我的国家,我的生活命中注定般充满了各种不可思议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过丝绸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过王子的金镯,奴隶的枷锁。我的手揭开过上千面纱,我的唇吻过上千女孩,我亲眼见证过城市的衰落和帝国的消亡。
你能听到我讲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柏柏尔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和通俗义大利语,因为我掌握所有的语言,会说所有的祷告词。但我不属于它们。我只属于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将来的归宿。」
来源:苹果日报
梁文道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ly/20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