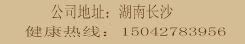今天是周六,我睡不着觉于是六点多的时候就下了床来到院子里看看我的小鸭子,它仿佛知道我要来一般,早早的就从纸箱做的窝里面走了出来迎接我,小声然后慢悠悠的叫唤着,它的脚上绑着一根细细的红色尼龙绳,我害怕它趁着深夜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跑丢了,于是在它脚上绑了根绳子,另一端系在墙上的铁钉上面。父亲周五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带回了这只可爱的小鸭子,当时他正骑着摩托车,这只小鸭子突然从路边的草丛里面飞快的扑了过来,两只脚一上一下快得像弹簧,爸爸赶紧刹车停下来,这只幸运的鸭子只差一点点就要被轮胎从它身上轧了过去,变成一团肉泥。父亲四下里观察了一下,这是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鸭子,附近也没有发现其他的鸭子,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还是落单了,于是就把这只可怜的小鸭子放在摩托车前面的篮子里带回了家。现在它成为了我的宠物。我早饭故意留了一点粥在碗里,带到小鸭子面前倒在给它准备的一个旧的搪瓷碗里面,然后用一个废弃的塑料杯子舀了半杯水放在它面前。它看起来好小只,孱弱的身子和纤细的小脚丫,身上披着毛绒绒的黄色羽毛看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一点也不害怕人,我伸过手去它会主动的靠过来,任由我抚摸它的小脑袋和身上的羽毛。它用扁扁的小嘴巴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啄了几下,感觉痒痒的,心里氤氲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暖意。我把它抓起来放在手心里,举高到我的面前仔细看着它,它侧着头用一只眼睛跟我对视,不知道在鸭子的视角看来,面前这么一个巨大的人对它来说是什么感觉,小翅膀扑腾了几下跃跃欲试想飞下去,我觉得有种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又说不上来,当我把它放下来看着它低头开始吃米饭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它跟之前陈秋葵送给我的那个毛线球做的鸭子玩偶挺像的。或者说是一模一样。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就叫它“秋葵”吧。我在心里偷着乐,打算等周一上学了,把这件事情告诉她。我养的一只小鸭子叫“秋葵”,我已经能想象到她那气鼓鼓的脸上挂着两个瞪得跟灯泡一样大的眼睛了。今天早上的天空姹紫嫣红,异常的壮丽。东方的地平线上就像铺了一条巨大的红领巾一般,被红色吞噬了。慢慢的有几缕金色从一抹鲜艳的红色中穿透而出,太阳升起来了。我想起了课本上的那句谚语——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难道这两天要下大雨了吗?我思考着应该把我的小鸭子安置在什么地方比较安全一点,就这么放在院子里太危险了,我这才突然想到最近经常有一直黑黄相间的流浪猫在曾祖母那间瓦片房上徘徊,它帮家里抓了好多老鼠但是也咬死了好多刚出生的小鸡,还好它昨晚没有跑进院子来,心里一阵后怕。我需要找一个可以遮风挡雨,太阳晒不到又不会有太多蚊子,也不会被野猫和老鼠咬死的地方。很快我便相中了楼梯角落下面的一个鸟笼,这个鸟笼是外公去年买来养一只鹦鹉的,不过鹦鹉买来没几天就因为妈妈喂完之后忘记关笼子飞走了,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它回来,于是就一直闲置在角落里,如今已经布满了灰层。我拿上湿抹布从里到外仔细擦拭了一遍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小鸭子脚上的绳子解开,然后放到笼子里面关了起来,再往里面的两个小盘子装了点剩饭和井水。我听到爸爸的摩托车启动了,赶紧叫上弟弟一起出门了,今天我们要去爸爸的工厂里面玩。爸爸在一家电池厂打工,离家大概三公里远。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木板钉成一个个货架,用来盛放电池。只有在出货的那一段时间会比较忙和经常加班,其他时间倒是挺轻松的。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在工厂外面一个独立的店面,所以平时也没有人监督他,他会偷偷跑到隔壁修理摩托的店里面泡茶聊天,偶尔会做做一些木工艺品,像是拐杖、椅子、鞋架还有一些木质的玩具车和玩具刀剑,他也会雕刻一些动物还有印章。不过今天他显得非常的忙,腾不出时间来陪我们玩。我跟弟弟坐在门口,面前就是国道,不过来来往往的车辆不是很多,以摩托车和面包车为主,隔一段时间会有大型的运渣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经过。马路对面是条铁路,每隔半个小时左右会有一辆绿皮火车轰隆轰隆从右边向左边疾驰而去。我和弟弟就在门口数着一共有多少辆火车经过,每辆火车一共有几节车厢,但是每次我们数出来的数量都对不上,为此争执不休。这整条路上都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也没有地下通道和天桥,很多想到马路对面去的人只能趁着车流量少的时候横穿过去,据大人们说,这里频繁会有撞到人的事故发生。有一次当一个老人正在横穿马路时,一个调皮的小孩突然大喊一声吓了他一跳,手慌脚乱的他来不及躲避车辆就被撞到了,大腿和肋骨全断了。此时又有一辆火车准备经过了,爸爸从店里面走了出来打断了我和弟弟数车厢。他告诉我们要去工厂里面见一下老板,有工作要汇报,让我们待在这里不要乱跑也不要乱动店里面的工具。我们应允了一声,他就急匆匆走掉了,临走前他跟店里面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交代了几句,他应该就是爸爸说的新来的徒弟,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左右,不会说闽南语,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北方口音。我和弟弟相视一笑,开始捣鼓店里面的稀奇玩意,一早上可把我们憋坏了。店里面堆满了木板拼接起来的货架,还有成堆的铁钉,铁锯,铁锤和米尺等等工具。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一辆红色的看起来像手推车的东西,它有一个高高的把手,底下是两个类似滑板车的分叉,每个分叉下面有2个轮子,最前面也有2个轮子。我双脚分开站在上面,让弟弟在前面拉着把手带动我滑行起来。后来我们发现了新的玩法,或者说是它真正的用途,我站在车子上面,然后弟弟由上往下地扳动把手,就像在给轮胎打气一样,每扳动一次我就向上升起几厘米,直到没办法继续上升之后,拉住把手上类似自行车刹车的装置,车子就开始下降,我也跟着慢慢降落到地面上。我跟弟弟轮流玩着这辆车,小徒弟偶尔会抬头看一眼然后又继续低头用铁锤敲打着铁钉,发出清脆又响亮的金属撞击声,感觉空气和耳膜都跟着震动起来。这次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双手放开旁边的墙壁,做出一个像雄鹰飞翔的动作,下降的过程中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摇摇欲坠,我情急之下就扶住了车把手下面较高的车身部分,一口气还没松下来突然一股剧烈的疼痛从食指指尖钻心而来,我扶住车身的时候把手指伸进了车身的缝隙里,下降的时候被夹住了。我疼得发出惨叫声,两脚不停地跺地板,剧烈的疼痛传达到大脑皮层,整个人眼前一片空白。弟弟却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一边笑着让我不要再装了,一边继续让车子下降,我疼得双腿发软跪在了地上,这时他才发现不对劲,一脸惊恐的看着我,旁边的小徒弟见状赶紧跑了过来,快速的按压把手把车子升上去,大概过了3秒左右,我终于把两只手的食指从车身里面抽了出来。两只食指红得发黑,食指指甲里面满满都是淤血,上半截手指已经肿了一圈,我尝试弯曲一下食指,发现食指已经不受控制了,不停地发抖,火辣辣的,随着心脏每跳动一次,食指就跟着发出一阵疼痛。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半天没有反应,我害怕我的手指是不是断掉了,直到小徒弟把爸爸叫回来之后,当他拿起我的双手仔细查看的时候,我突然崩溃了,放声大哭起来。爸爸赶紧带着我跟弟弟回家去了,一路上三个人都不敢说一句话。弟弟因为内疚始终低着头,爸爸骑着摩托车脸色凝重的望着前方,我的脑海里只有疼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次回家我们三个人免不了都要挨一顿骂。送弟弟回家后,父亲掉头带着我到附近的诊所里面让医生给我的手指敷药。医生是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蓄着山羊胡子,但是头顶却已是童山濯濯。所幸的是,只是皮肉苦没有伤到筋骨,医生为我消毒之后敷了些止痛和消炎药上去,简单用绷带包扎了一下之后就结束了。等淤血消去,疼痛消退后就没有大碍了,手指依然可以正常的写字和运动。回到家后,一进门就看到妈妈脸色显得十分难看,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十足的火药味,稍微有一丁点儿火花便会发生巨大的爆炸。“你的手怎么了?让你待在家里不听,非要跟着去厂里,现在开心了吗?”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拉到她胸前仔细观察着。“我刚好进厂里面跟老板汇报工作去了,他们两玩着千斤顶,手指不小心伸进了缝隙里面,下降的时候被夹住了,好在旁边有人及时帮忙松开了,只受了点皮外伤,指甲里面淤血了。医生说要一周左右才会恢复。”爸爸的语气十分小心谨慎。我看到妈妈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去吃饭,吃完去洗澡!”她凶狠的命令我。我此刻就像笼子里的那只小鸭子一样温顺,不敢有任何意见,只能唯命是从。我清楚只有这样,我接下来几天才能过得不那么痛苦。我现在不管做什么都只能竖着两根食指,端饭碗,拿汤匙还有筷子,还好不是中指,想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然后马上又恢复严肃,回过头确认了一下妈妈没有在看着我。这时房子后面的小巷子有人急匆匆的跑过去,脚步缭乱,看样子像是有什么急事,他在门口朝我们家里大喊:“赶快把家里顶楼收看台湾电视台的天线还有机顶盒藏起来,村里来人抓啦!”话还没喊完就朝着下一家跑去通风报信了。最近村里面许许多多户人家都在楼顶装上了收看台湾频道的天线还有机顶盒,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装起来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口口相传都在讨论台湾的电视节目如何如何有趣和精彩,纷纷通过熟人介绍安装了起来。我们家也加入了这一股潮流当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的电台实在是太无聊了,过于官方还有死板;另一个原因是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台湾民视八点档的节目可以预测六合彩,好多中大奖的都是看这个节目的,于是村里一堆赌徒就竞相奔走相告装起了。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国内跟台湾的局势是非常微妙的,战争仿佛随时都可能爆发,处在台湾对岸这个地方自然更加政治敏感,镇上好多工厂都是台湾的商人过来投资设厂的。村里隔三差五的经常会有人来搜查,一旦发现有谁家里安装了这类天线和机顶盒一律拆除没收并且还要到村委会接受批评教育。我们家上个月已经被拆掉一个机顶盒了,那时候才四点多,家里就只有外公和外婆两个老人家在,突袭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只能看着他们硬生生拆除掉机顶盒带走,不过好在天线还在,爸爸后来又花了点钱重新买了一个机顶盒装上去就又可以继续收看了。最近我们全家都在看一档名叫《亲戚不计较》的节目,已经播出了将近两千集了,讲述的是粗皮雄与卓有春这两个从小斗到大的欢喜冤家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琐事。后来村里有一些人自发去当了“探子”,专门通风报信,就像刚才那个人。爸爸赶紧把机顶盒拆了收到房间里面去,楼顶的天线也赶紧藏了起来,过了不到几分钟就有几个来势汹汹的中年人涌了进来,一进大门二话不说就朝着客厅里面走去,东看看西瞧瞧,这边翻一翻那边掀一掀,他们手法不算粗鲁也没有进到房间跟楼顶去查看,在客厅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悻悻的就走了。“跟那时候的红卫兵比起来,十分斯文了。”外公坐在石凳上一边用蒲扇扇风一边说道。更小的时候听外公说起过,他年轻的时候见过村里红卫兵搜家的情况,翻箱倒柜,家里全部值钱的东西都揣到裤兜里带走,带不走的就全部砸了,然后把人带到田里面绑起来暴晒,很多人都没有熬过来。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龙眼树被吹得摇摇欲坠,树枝和叶子四处飞舞,我抬头望着天空,这才发现乌云密布。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大概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暴风雨就来了,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台风,根据昨天晚上的天气预报说,这次的台风有十一级左右,大概在今天凌晨两点抵达。风在外面呼嚎大作,吹得窗户哐哐作响,风从窗户的缝隙吹了进来发出如同小孩呜咽一般的声音,硕大的雨滴拍在窗户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我被这些声音吵得睡不着,生怕窗户被雨给砸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入睡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风力已经减弱了,现在只剩下毛毛细雨在空中飘着。院子里面一片狼藉,盆栽被吹倒了好多,折断了的龙眼树枝落满了院子,前院的那棵枇杷树被连根拔起,横倒在门口。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关着小鸭子的那个鸟笼现在躺在院子正中央,笼子的门开着,里面的鸭子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把整个院子找了一遍,甚至厕所、楼梯下面还有前院都翻遍了,就差掘地三尺了,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影。我的小宠物短暂陪伴了我一天之后就宣告失踪了,都还没来得及跟陈秋葵说这件事,心里难免有些落寞。过了一周之后我的手指终于可以拆掉绷带了,已经没有疼痛感了。只不过我的两只食指的指甲黑得像木炭一样,并且根部已经脱离皮肉了,看起来是要脱落的样子。我担心的问妈妈:“指甲还会重新再长出来吗?”“过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了,没关系的,这段时间小心一点不要刮碰到就好了。”我看着自己的两根食指,食指最后一截的肉里面有一道白色的痕迹,就像一道隔膜一样。仔细触摸的话会有异物感和凹凸的感觉,这道伤疤估计要伴随我一辈子了。晚上做完作业后我忽然想起来陈明玕的日记还有一半没有看完,我准备带到楼下去看。等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发现楼下声音有点吵闹,仔细一听发现声音是从饮食间里面传出来的,除了爸爸的声音之外还有两个男人的声音,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偶尔会哈哈大笑,并且互相劝酒,时不时发出杯子碰撞的声音还有啤酒瓶盖打开后啵的一声。估计是爸爸带同事或者朋友来家里喝酒了。我下了楼梯后直接进了客厅,见到妈妈正板着一张铁青的脸伏案记账,一边用计算器在算些什么,一边把结果写到本子上。看得出来她的心情糟糕透了,她向来不喜欢爸爸的那些狐朋狗友,每次他带朋友或者同事回来她总是不待见,显得十分不耐烦,映象中就没见她给过好脸色。爸爸带回家的人多数是他的老乡华安那边的人,妈妈对他的老家有着很大的偏见。台风才刚过去没几天,我不想被台风尾巴波及无辜,于是安静的坐到另一边的椅子上阅读者陈明玕的日记。八月份的日记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七月份的如出一辙,基本上全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事。然而,就在我逐渐失去阅读的兴趣时,有篇日记的片段却让我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狂喜。“我跟她约好了一起去秘密小基地那里见面,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才知道的地方。基地就像一个小帐篷,躲在里面像山洞一样,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抓萤火虫来这里,静静的看着它们。她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心情就一直很低落,我决定要想办法让她开心起来。我现在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老师或者其他人这件事,但是说出来的话对她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她是谁?基地是在哪里?那件事又是指什么事?我带着满脑子的问号继续阅读下去,企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时候院子里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来,我们来跳舞。”看起来像是有人喝醉了。爸爸的酒量非常好,自从我出生到现在就没有看见过他喝醉,而且他也不敢在妈妈面前喝醉,显然是爸爸带回家的另外两个人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喝醉了。我听到有人在唱《上海滩》的音乐。看来醉得不轻。我在心里想着。爸爸拉着他想让他进屋里面坐着休息一下,不过他拉着爸爸的手摇摇晃晃的好像在跳探戈。爸爸和另一个人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硬拉进来,他一屁股靠着客厅大门瘫坐下来。我用眼角迅速瞄了一眼,他已经是一滩烂泥了。留着长头发,穿着一件纯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脖子上挂着一个金属链子,看样子估摸有三十来岁。我继续低着头阅读日记,我已经闻到硝烟的味道了。妈妈仍然低着头在算账,这时候那个酒鬼看到妈妈突然扑腾起来坐到了长沙发上,紧挨在妈妈旁边。我的心跳加快了起来,心思已经不在日记本上了,十指紧紧地攥着日记,脱落了指甲盖的两只食指发出了一阵疼痛。那人低着头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从侧面看着妈妈,妈妈则始终埋头算账没理他,我听到他喊了一声:“来跳舞啊。”我紧紧地咬着牙齿,感觉牙齿随时都可能崩断,我侧着脸瞪着他在心里倒数着,再过十秒他要是不从妈妈身边走开我就要用拳头砸在他的脸上还有鼻子上,最后再给他的嘴巴上来几拳,把他的门牙全都砸下来。就在我倒数到3秒的时候,爸爸和另外一个人把他拉开,喊着说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可是刚把他从长沙发上拉开,他又挣扎着想坐回去。我看到另一个人死命拉着他想把他拽出大门,一脸尴尬和愧疚的表情,爸爸则是捏紧了拳头脸色铁青,两个人合力把他拽了出去,走到院子大门口的时候我还听见他嘴里歇斯底里不停在喊着跳舞。等到爸爸回来之后,妈妈就彻底爆发了。家里场面十分混乱,只见妈妈不停地大声斥责着爸爸,爸爸则是一言不发任由妈妈骂着,不过这样反而更加激怒了妈妈,一怒之下她把桌上的东西全砸了。外公和外婆也跟着妈妈数落爸爸的不是。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愤怒中缓过来,在心里对爸爸也是十分生气,我不懂为什么他不好好的把那个小瘪三修理一顿,用他平时劈开砖块的力气把那个人劈成两半。我始终一言不发的坐在旁边继续看着日记,对于他们的争吵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我觉得大人之间的矛盾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小孩子不应该掺和到里面。日记的最后一篇让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看了一眼日期就在陈明玕发生意外的前一天。陈明玕在日记里面写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我神经敏感,我总觉得有一个陌生人老是在我们家附近徘徊。有好几次我在屋里看到他在四处张望,不停地探头观察我们家的情况。”又是那件事,我想我有必要弄清楚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日记那一页的背面用铅笔画了一张脸,这张脸跟刚才在家里耍酒疯的那个人居然如此的相似?这是巧合吗?我在脑海里搜索着陈明玕曾经跟哪个女同学比较亲近,可是一个都没有,是他家附近的邻居小孩吗?小基地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学校吗?还是他家附近?他跟那个小女孩遇到了什么事让他难以启齿?就在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的战争已经停下来了,全家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我的指甲在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发现已经脱落了,就掉在了枕头下面,我把它们捡起来,乌黑发亮的,用纸巾包裹起来放到了书桌的抽屉里面收起来。
..................。。。。。................
ID:Zeroorez93
主要发布文学、自然、科普、心理学、新鲜事、哲学、历史和幽默趣闻等原创或翻译作品。不定时更新,爱看不看~
Strong
AmazingGrace.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jj/8699.html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连载萤火虫消失的地方六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连载萤火虫消失的地方六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连载萤火虫消失的地方六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连载萤火虫消失的地方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