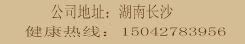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马琳瑶胡达middot巴拉卡特写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马琳瑶胡达middot巴拉卡特写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马琳瑶胡达middot巴拉卡特写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马琳瑶胡达middot巴拉卡特写
一、作者与作品
(胡达·巴拉卡特)
胡达·巴拉卡特,年生于黎巴嫩小城比沙里(?????),自幼成长在基督教马龙派教徒聚居的黎巴嫩北部山区,青年时期前往首都贝鲁特求学,年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并于毕业后短期任教于黎巴嫩南部村庄希亚姆(??????)。内战爆发后,她迁回比沙里,并于-年间赴法求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战火纷飞的故乡始终萦绕着她,终于她放弃学业,重返故乡,并先后从事教师、记者以及翻译等多种职业。此外,她曾任职于黎巴嫩研究中心,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并于年参与女性杂志《山鲁宰德》(Shahrazade)的创刊。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访客》(????????)标志着胡达·巴拉卡特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开端,五年后其小说《炼笑石》出版并获得“评论奖”(??????)最佳处女作,次年移居法国,并在“东方电台”(RadioOrient)担任信息主管。年和年分别发表《幻想的人》以及《耕水者》,年发表散文集《陌生女人的来信》[1],并于同年发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年发表第五部长篇小说《这片土地上的王国》[2]。年,其最新小说《夜间来信》发表,并获得年“国际阿拉伯小说奖”(IPAF)(亦称“阿拉伯布克奖”)。在创作小说之余,胡达·巴拉卡特在年和年分别发表戏剧《Diva万岁》[3]以及《夜之将尽》[4],其中前者由黎巴嫩方言写成的。
自年《炼笑石》[5]出版起,胡达·巴拉卡特便凭借其处女作,树立起她在阿拉伯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革新者形象。该小说则因为“哈利勒”——阿拉伯现当代小说中第一位同性恋主人公——在阿拉伯世界以及欧美学界引起一系列讨论。年移居巴黎后,胡达·巴拉卡特在异乡继续其文学革新历程,年她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幻想的人》[6],其中涉及“雌雄同体[7]”、“跨宗教情侣”等争议性话题以及对性爱场景的直接描写,这些使该小说在发表后的近三十年间始终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年其第三部长篇小说《耕水者》[8]问世,两年后获得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写道:“(该小说)兼具文字的魔力和见识的广博,它既吸引我们又教育我们。”年,胡达·巴拉卡特发表其第四部长篇小说《我的主人,我的爱人》[9],作者通过讲述“瓦迪”对其性别身份的探索,审视了内战时期的黎巴嫩社会,批判了该社会中的暴力、不公以及父权制度。
以上四部小说构成胡达·巴拉卡特笔下的“黎巴嫩内战四部曲”[10](以下简称“内战四部曲”)。尽管其发表时间跨度较长,创作背景也不尽相同,但是读者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共同的主题:对于被社会两极化性别准则边缘化的性别身份的探寻。四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均为男性,但是他们或是因为其同性恋身份,或是因为其性取向的不确定性,亦或是因为其对于霸权男性气质的拒绝而无法满足外界对他们的期待;同时,他们均在不同层面以及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所谓的“女性气质”。由此,可以看出“性别策略”在胡达·巴拉卡特的“内战四部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作者在“内战四部曲”中选择由男性叙事者来讲述整个故事,这一“跨性别”的叙事也构成胡达·巴拉卡特的性别策略中的一部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当我在写作时,我走出自己的性别,不论自己的哪种性别。在我看来,写作是不同寻常的,它超越男性或者女性的行为特点或者行为规范。或者说(写作)正是在男性与女性的严格界定以及模糊这一边界的欢愉的交汇点上。或许创意写作的精髓便在于对于性别的模糊,就像植物传播花粉以及大自然静谧的和谐。”[11]
(胡达·巴拉卡特在年巴黎“东方与马格里布“书展)
二、胡达·巴卡拉特与性别写作
性别观念在胡达·巴拉卡特文学创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纵观内战四部曲,主人公们的性相(sexuality)在小说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本身的性别身份也参与其中,巴拉卡特身为女性,却在这四部小说中将叙述聚焦于男性人物形象之上,从他们的视角开展故事,使其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也参与到其性别策略的整体中。
四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无论其本身的性别取向,具有一个共同特点:生理性别为男性的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谓的女性气质,与此同时,他们渴望强化自身的女性气质。他们作为男性被要求具备的男性气质与他们自身所渴望的女性气质之间的矛盾推动故事的发展,又因为该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导致故事的终结。在综述这一特点的过程中,“雌雄同体”[12]这一文学传统引起本文的注意,是否可以说这就是巴拉卡特在“内战四部曲”中运用的首要性别策略?
胡达·巴拉卡特并不是阿拉伯文学领域第一位触及“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的作家,在她之前埃及作家优素福·伊德里斯和纳瓦勒·萨阿达维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主题有所涉及。伊德里斯在短篇小说《谢赫·谢哈》[13]中塑造出一位性别模糊的主人公,这一人物最终因为村民们对它的怀疑与猜忌而惨遭杀害。萨阿达维在《旋转的歌》[14]中设置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哈米达”与“哈米杜”,将他们刻画为“雌雄同体”这一概念中两性的分别体现,并通过他们来打破建立在两性等级制度上的父权制度。
巴拉卡特在访谈中谈及自己对于“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解时说道:“这个说法年代久远,是柏拉图提出的,完美的生物,完全的生物是拥有一切的,他不再需要外界,因此他获得了自由,对于我来说,雌雄同体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是一种自由。你拥有了一切,不再需要为了获得另一方而受到煎熬,你所想要的另一个人可能和你非常的不同。你拥有一切,一切都得到了平衡,但是这同时也会扼杀你的各种欲望,这个哲学观点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一点很吸引我。[15]”结合作者自己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以及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解读,本文将对以下人物形象进行研究:《炼笑石》中的哈利勒,《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以及乌姆·库勒苏姆,《耕水者》中的尼古拉以及哈努和《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的瓦迪。
????????
(????)
哈利勒的“雌雄同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他的体格,他的行为以及他面对战争时所选择的立场。他的“雌雄同体”不仅仅是其柔弱、多愁善感和对同性的迷恋,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于外界不适时的天真的认知。在黎巴嫩内战的社会背景下,他面对杀死敌人和被敌人杀死的选择,但是,他试图拒绝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他也因此注定最终在道德层面自我沦陷,按照外界对他的期待去参与战争,他注定要为了自己继续生存下去而杀死本来的自我。哈利勒最终放弃“雌雄同体”的自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幻想的人》中的男主人公所表现出的“雌雄同体”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概念更为接近,男主人公渴望与他的女性爱人[16]构成两性的和谐统一体。在社会层面,两位主人公的结合同样也体现了作者对于男主人公代表的基督教和女主人公代表的伊斯兰教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希望。然而,两位主人公在短暂地实现“雌雄同体”这一理想之后,即开始分崩离析,男主人公感到女主人公对他的个人空间的入侵,同时女主人公的存在加强了他面对生活的无力感。加之女主人公多次离他而去,最终,男主人公走向了自己虽追求的一切价值的反面,他亲手杀害女主人公,并试图以此来弱化自己有违于时代背景的“雌雄同体”的追求所带来的痛苦与磨难。此外,小说中对乌姆·库勒苏姆的再现与男主人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疑惑相互映衬,作者将她塑造为一个同时具有男性声音和女性声音的完美存在,同时她也是男主人公追寻的“雌雄同体”的化身。
《耕水者》中的辅助人物哈努是一位女性化的男性人物,他在小说中与尼古拉的父亲产生冲突。“雌雄同体”在他身上既体现在他的外貌与行为中,也体现在他对战争的漠不关心以及他对尼古拉父亲的权威的挑战中。“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在小说主人公尼古拉身上体现为他对于过去的追忆,即哈格里弗斯在研究中提出的,雌雄同体的人物可能代表对过去的思念。他通过和情人杉姆赛的交谈,回顾纺织业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布匹来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他在战火中四处躲闪,试图在废墟中找到父亲曾经经营的布料店。然而,他最终没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只能在亡命街头。
“雌雄同体”在《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主人公瓦迪身上可以简单概括为双性恋和两性特质的共存。儿童时期的瓦迪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具有所谓的“女性特质”,他因为柔弱而遭到同班同学们的霸凌,同时他不自觉地暗恋好友阿尤布。家庭生活中的突变使瓦迪选择辍学,加入街头帮派,迎娶邻家女孩萨米亚,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金钱与权势,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树立自己的“男性气质”。然而,生意上的意外失手使他不得不逃离黎巴嫩,流亡塞浦路斯。这一打击击垮了瓦迪辛苦经营的男性气质,也使他同时失去社交能力和性能力。在逐渐回归生活正轨的过程中,瓦迪结识了工作中的上级塔立格,并最终认清了自己的双性恋事实,并希望通过自己与塔立格的关系重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塔立格在工作中利用他,借他顶罪的事实对瓦迪造成致命的打击,他最终消失,不知去向。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对于“雌雄同体”提出以下定义:它首先代表对于两性和谐统一的追求,同时也是作者对“父权社会”以及它所强加的“男性气质”的挑战。此外,“雌雄同体”在本文中也做形容词使用,用于修饰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其他名词,具体含义因上下文的语境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胡达·巴拉卡特(左二)获得年阿拉伯布克奖)
三、策略运用中的得与失
????????
(????)
胡达·巴拉卡特通过塑造《炼笑石》中的哈利勒、《幻想的人》中的无名男主人公、《耕水者》中的尼古拉和哈努以及《我的主人,我的爱人》中的瓦迪这些“巴拉卡特式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预期打破性别桎梏,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气质的单一呈现,并试图通过该策略来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统一,甚至打破性别界限,创造出“雌雄同体”的理想化存在。但是,这些人物形象最终却无法逃脱自身的追求使他们所处于的困境,也就是说,“巴拉卡特式雌雄同体”的人物形象因为“雌雄同体”的理想而最终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巴拉卡特的性别策略也因此陷入自身的矛盾。也就是说,作者的性别策略在运用的过程中有得也有失。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并审视了战争机制和父权社会,但是同时又受制于这两者以及在这两者作用下所产生的性别话语。
当代黎巴嫩文学经过十五年的战火洗礼,被打上深刻的战争烙印。黎巴嫩战争文学在重现现实的同时,避免了单一的战争话语,它不仅囊括了对战争的描写,还通过语言的创造性运用突破现实的界限,超越了传统叙事的条条框框,此外,它还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描写,敢于将叙事沉浸在个人和集体的回忆中[17]。这个时期的作家们通过描写战争给个人带来的创伤,描写各种战争的疯魔,甚至通过提出对理应承担战争责任的集体的控诉,来实现诗人阿巴斯·贝伊顿所说的“战争不只是一个丑闻,也是一种社会程序,一种现实或者潜在现实……不只是一种罪行,还是一种文化进程,一个立场的集合”[18]。
在黎巴嫩战争文学的创作群体中,有一个被米利亚姆·库克称为“贝鲁特离心派”(BeirutDecentrists)的女性作家群,其中包括嘉黛·艾勒-萨曼、哈南·艾勒-谢赫、黛西·艾勒-埃米尔以及艾米丽·纳斯尔拉等,这批作家集体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文学作品,通过描写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媒体和政治话语不曾触及的一面,旨在记录战争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战争如何成为一种日常。此外,她们写作的主题还有黎巴嫩首都和乡村之间的差距、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之间的冲突以及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行为预期等[19]。她认为“只有女性文学可以记录通常无法被注意到的看起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但是,正是这些细节所隐含的转变描绘出每个个体的战争经历的篇章”[20]。库克的研究由于发表时间早于《炼笑石》的出版时间,所以未能将胡达·巴拉卡特列入这一作家群,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作品与“贝鲁特离心派”的作品共享这些创作主题。诚然,巴拉卡特笔下的主人公均为男性,但是这些男性角色或多或少都带有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特质,也就是上文中所研究的“雌雄同体”这一特点。此外,其描写的主要内容同样为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战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其对个人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渗透,并以此对个体造成难以平抚的创伤。
脱离主流战争话语的“离心”写作既是这一作家群审视和控诉战争的方式,也是胡达·巴拉卡特写作的轴心,她善于塑造边缘化的人物,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jj/4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