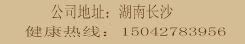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十日谈这个小女孩的理论水平太高了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十日谈这个小女孩的理论水平太高了

![]()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十日谈这个小女孩的理论水平太高了
当前位置: 萤火虫 > 萤火虫的习性 > 十日谈这个小女孩的理论水平太高了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教导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守法者,长大以后,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见义勇为,却不屑于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标志。仅次于教育的是奖惩,或者说奖惩也是教育手段的一部分。奖不止来自官方褒扬,更来自路人赞许的表情和手势;惩不光来自警察罚款,也来自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
这里推荐的内容全部来自思想潮(ID:sixiangchao)年9月16日-26日推荐的精彩文章。如果您此前错过了,可通过这里精选的章节来补上;如果您已经读过了,可以通过这些摘选回顾一下;如果您此前未 王蒙(作家、原文化部部长):
“尊重差异,互相交流,互相包容,互相欣赏”,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理念。不是因为有差异我就讨厌你,我就看不起你。如果没有差异,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方式,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
中国有一个大学者费孝通,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世界学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提出来一个口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每个人都可以认定自己美好的东西,同时也要看到别人美好的东西,虽然不一样,美的东西我们可以共享。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针与口号。
伊斯兰教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不崇拜偶像,不搞具体的偶像崇拜,不把真主人格化。有一次我与伊犁农村的小女孩,她可能也就4-5岁。那时我正在努力地学习维吾尔语,我见到谁都愿意聊天。有一次我就指着上天说“真主在天上”。她就告诉我说“老王,真主不在天上,真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厉害一个小女孩,她的理论水平太高了!我们在宗教里需要寻找的是一种终极的概念。宗教并不是说哪里有一个神仙,月亮上有神仙。人已经登上过月亮,那上面没有神仙,火星上也没有,神是在你的心里。在这些方面,伊斯兰教都有很先进的地方。它与天主教、佛教一起,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之一,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是阿拉伯人写的,阿拉伯人在数字方面也有很多贡献。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贡献,都不需要我去细说。但是,我们同时又要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伊斯兰教究竟是向开放上走,还是向排他方面走。现在有很少数的人,这些人当然不能代表伊斯兰教,但他们在向排他方面走。
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年轻人库尔班江,他是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他在那里工作得也非常优秀。他在全国采访了多个从新疆来的,在口里各地打拼的,多半是成功人士,也有正在打拼,还不那么成功的。有带着孩子在读研究生的,开餐馆的,卖羊肉串的,大部分是在内地在现代化的大潮当中相当成功的来自新疆的各族同胞。其中有一个美女,现在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收入与威信都很高。在他们的身上让人看到的是光明,不是黑暗,不是仇恨,不是焦虑,不是不安,不是尴尬,不是痛苦。因为他们乘上了现代化这趟列车。现代化不是万无一失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现代化使你离自己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由于现代化,你有了实力,你可以回过头来做大量的保护、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
我们不能把现代化与民族文化对立起来,我们要追求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好地来保护、弘扬、继承、珍惜我们的传统文化。用拒绝现代化的方法,你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拒绝现代化的结果,只能是民族的衰微与灭亡。
这种焦虑不但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有,汉族也有。在拒绝现代化的前提下,你的文化更混不下去。
——摘编自年9月17日思想潮推荐的《新疆的现代化焦虑与民族传统文化》
邓子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瞥一眼斑马线,就能立刻体察到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斑马线是现时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一处莫大的隐痛,它隐隐作痛,正是不断提醒我们:温良恭俭让的世情民风正在远去,法治之下的和谐敦睦还没有到来。
行人不走斑马线,无视红绿灯,有很多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目的轻手段,或者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成效轻规则。哂笑“只看红灯绿灯,不看有车没车”,与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脉相承的,暴露出国人聪明算计背后的功利和短视。每当想到别人可能一样聪明时,国人的解决方案是让自己更聪明,更胜一筹,而不是共同回归规则。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一旦不守规则,自己就吃亏了,还不如自己先把规则端掉。宁可自己不受益,也不让别人得好处,也就是所谓“损人不利己”。并且,过去若干年,我们滥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其庸俗化,喜欢一切操之在我,推崇相机而动,挞伐教条僵化,鼓励便宜行事,贬斥墨守成规。视规则为束缚,视遵守规则为呆傻,不愿忍受遵守规则的代价,乐于玩味突破规则的利益,又总是相信,破坏规则的恶果只由别人承担,或者别人和他共同分担,而自己却能独享其利。
国人不敬畏规则,只惧怕规则背后的人。为什么摄像头比信号灯更有威慑力,因为人们相信它背后有一双权力的眼睛。毋庸讳言,规则不受待见还缘于路面上有太多的特权车,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频繁地破坏规则,在百姓中不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一万次法制宣传,也经不起一次对法规的凌驾。因此,在许多人心目中,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我问过几个瑞士人,开车时为什么礼让行人?他们的回答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从何而来?我以为来自教育、奖惩和模仿。就斑马线上的国民表现而言,不得不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是失败的。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教导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守法者,长大以后,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见义勇为,却不屑于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标志。因此,斑马线问题,应当从娃娃抓起。仅次于教育的是奖惩,或者说奖惩也是教育手段的一部分。奖不止来自官方褒扬,更来自路人赞许的表情和手势;惩不光来自警察罚款,也来自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我曾设想,能否让汽车也有“表情”,民间可否发明一种“灯言手语”,说“请您先走、谢谢、对不起、没关系”。不过,如何确保让汽车只说礼貌话,不说骂人话,倒真是个问题。说到模仿,当今世界不乏公认的、现成的好榜样,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模仿。
斑马线是具体而生动的全民法治的课堂,应当在这里学会建设无需权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严和自治。
——摘编自年9月21日思想潮推荐的《斑马线上的中国》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
当古希腊人把“勇气”当成一种“公民美德”来构想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头想的一定不只是个人面对僭主和独裁者的勇气,而且还是一个公民(甚至主要是)独自面对其他公民以及整个城邦的勇气。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太过偏重前者,喜欢歌颂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知识人如何敢于对权力者说真话;却忽略了他对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citizens)说真话原来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请注意,这里所指的“真话”,并非客观上一定正确,近乎真理的言论;而是发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个人信念与价值的话。
由于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亟需每一个公民都能畅所欲言,所以说真话的勇气才算得上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公民美德”。不过,我们可以换个面向来看,这样子的民主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每一个个人都敢对不赞成他的大众说真话,它最好还得降低一个人的恐惧,减少他说真话的成本。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合底下说真话也许是不可怕的,即便你的意见太过偏锋,即便你的对手是一大群朝夕共对的熟人,你也不必担心他们以后会对你怎么样。该说什么你就尽管说,说完也就算了,没有人会把它挂在心上,和你断绝来往。
如果你是一个取向十分认真,把支不支持某种立场看成天大道德问题的人,你或者可以在媒体和网上替自己营建一个首尾一致的社群世界。可是当你一走出大门,用自己的双脚走在这座城市的道路上时,问题就来了。也许你天天在那里吃饭的食堂老板就是个立场不同的人,你要不要自此罢吃明志?也许那个会在你满手杂物时主动替你开门的保安就是个偶尔在网上发牢骚的,你要不要建议管理公司炒人?也许你的下属是个老爱把西方挂在嘴上的,你要不要想办法把他弄走?也许你的老板喜欢私底下阅读你不喜欢的书籍,你要不要勇敢地辞职抗议?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思考的时候不抽空不离地,真实地视自己为参与者,真实地把自己置放在具体而现实的处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选项。天天在网上痛骂的老师,应该想想如何面对自己班上的学生;认为名人移民全是不爱国表现的人,应该考虑万一自己亲友也跑去申请绿卡的情况。这样子的思考,方有责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体现。
——摘编自年9月24日思想潮推荐的《怎样才算“政治成熟”?》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美国的话语主导权建立在本国肥厚的观念土壤里,我们很难在大问题上听到一个“统一的”美国声音。可以说,如果美国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话语主导力。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对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常态。稍好一点的美国大学,也一定有训练学生作尖锐而理性辩论的常规资源(这与“愤青”式的骂街有天壤之别)。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她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
多元化的声音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即使美国的某项政策糟糕得不得了,但也只影响到美国一届政府的形象,对美国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影响则有限。一个国家长期发出单一的声音,只能使该国在国际上展现一种固定的面孔、单一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脆弱,易受伤害,多元的声音则使一个国家具有更加多面、立体的形象。
美国产生形形色色观念和论点的肥厚土壤,主要不是由美国政府提供,而是由美国社会提供。能够支撑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主导权的要素是深层次的,包括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大学,多种价值取向的研究机构,在自由竞争中优而胜之的媒体和从业人员,政策变更改善的制度性渠道等等。只有这些,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持续产生新观念和观念表达新方式的肥厚土壤。一个国家拥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使之在各个领域的大论战中从不缺席,让其他国家对她更加看重。
——摘编自年9月16日思想潮推荐的《美国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何以可能?》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边疆是个矛盾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它既危险又神圣,既匮乏而又潜藏着无穷财富与希望,它经常被忽略但有时又被深切 然而边疆也是国家的资源边界地带,因此在国与国之间的资源竞争中,边疆又变得十分神圣,值得人们抛头颅、洒热血去维护它。边疆的“边缘性”主要来自于资源竞争与匮乏。它或因政治强权间的资源竞争与分界而成为边疆,更常因资源匮乏而成为边疆。然而对于核心地区的穷人、失败者、不满现实者来说,边疆也是充满无主财富与无限希望的真实或想象乐土。
边疆不仅因其自然资源、地理空间、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地位而成为边疆,且被来自核心的人们观看、描述,而强化其边缘、边疆性。近代以来又出现两种背离前者并彼此矛盾的边疆话语;一为美好自然环境、独特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原生态生活、绿色食品、朴实民风,一为教育、开发、团结、维稳与现代化。这些对“边疆”的观看与描述,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距与矛盾,呈现的是人们对于“边疆”不足、错误且有偏见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些得自于边疆的知识讯息,强化我们所熟悉的知识体系,说明什么是合宜的服饰、正常的饮食、进步的宗教、可信的历史,以及高尚的道德伦常与政治社会秩序。同时,我们也被禁锢在这些知识所造成的世界中,而难以察觉周边事物的本相。
——摘编自年9月23日思想潮推荐的《建“民族”易,造“国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
黎蜗藤:
英国允许自古以来属于英国的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粉碎了俄罗斯所指的独立公投是西方国家“搅乱”世界的阴谋的说辞。它清楚不过地体现了西方国家所推崇民族主义,即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普世价值,而不是什么“双重标准”。
——摘编自年9月18日思想潮推荐的《“自古以来”属于英国的苏格兰能否成为独立国家?》
刘家驹(原《炎黄春秋》副主编):
年秋,我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摘编自年9月19日思想潮推荐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龙应台(作家、台湾“文化部部长”):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摘编自年9月20日思想潮推荐的《刚解严时的台湾》
卜昌炯(媒体人):
薛飞和杜宪的播音生涯同时结束于年代末。脱离了体制的他们,就像是从冰山上解冻下来的两个小冰块,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不得不独自掌握自己命运的风帆。在满是碎冰的海域上,他们会漂浮多远,会不会很快融化,他们并不自知。
薛飞说:“我从未想到过离去,也没有理由离去,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燃情岁月。”他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夏夜,他和妻子及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一起坐在北京西单“万国啤酒厅”畅饮,很多人都醉倒了,其间他朗诵了一首诗:当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凝望着血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诗人食指于年创作的《相信未来》,曾是很多人在“文革”时的精神支柱。当时流传有多种手抄版本,薛飞朗诵的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唯一会背诵的诗。
同样是离去,杜宪似乎没有太多留念,只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后顾之忧”,但一转念,觉得“想不了那么远了”。
年,他们一同入职央视,10年后又同时离开,投身商海,而今又都隐居大学校园,他们的人生轨迹看上去几近相同,但每个人又有自己不同的波段和频率。
“皓月”和“天蚕”分别是杜宪和薛飞离开《新闻联播》后用过的笔名,意味深长,暗暗指向他们的人生。
虽然远离公众视野多年,但薛飞和杜宪并没有被时光湮没,任何一丁点儿关于他们的动态,最后都会成为新闻。偶尔还有人在网络上贴出自己与他们中某个人的合影,以表达某种情怀。
——摘编自年9月22日思想潮推荐的《心如皓月,命若天蚕》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单靠自身力量,中国或美国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中美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中美不合作,世界将分裂成相互对立的阵营。我之前提到的各股势力,必将利用他国之间的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中美合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但前苏联几乎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中国与世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影响力主要基于经济表现而非军事实力——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同样,中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日渐衰弱,中国正在崛起,而衰落中的大国总是试图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因此某些冲突不可避免。他们举的例子就是英德对抗。英德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政策的短见。
中美一旦发动冲突,后果会更为惨烈。两国领导人明白,无论学术界持何种观点,中美不能对抗。这话我们很多人说了20多年,还不时遭到批评。然而现状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携手并不容易,因为中美做事的根本方式有所不同,两国的历史更有天壤之别。美国从未有过强大的邻国,中国却无时无刻不受近邻强敌的威胁;美国人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中国人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如何弥合两国的分歧,这是当代最大的挑战。
话说回来,基于我对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的了解,我相信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及现实给美国带来的变革,奠定了两国重启真诚对话的基础。尽管前路漫漫,争议不断,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摘编自年9月25日思想潮推荐的《中美关系:阻力与动力》
李泽厚(哲学家):
我从来不认为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政治民主,所以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但我也一直认为,经济发展是今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法治)的前提。虽然经济发达也可以出现希特勒、史达林,经济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因素,并非随时随地可以决定一切;但就整个人类历史的宏观进程和一般的长期情况来看,经济却仍然是政治、文化、心理等等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为甚么现代的民主、法治不能普遍地产生在中古时代产难道与近现代以科技—大工业为动力的社会经济没有关系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法治从何而来产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如何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有效而持久的法治?是靠几位知识分子、学者教授提出或宣传一套学说理论、思想主张以启蒙大众或说服当局来实现呢?还是通过在目前迅速发展中的经济领域内的各种立法、司法问题的具体落实、扩展而逐渐实现?我并不忽视前一方面,即学者、专家有责任有义务提出和宣扬各种思想、学说、建议、主张来促成现代民主—法治。
从八十年代起,我就一直反对新权威主义,主张逐步开放舆论言论自由等等,正是注意到经济发展可以导致或巩固专制政权。但我更重视目前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如各种旧秩序、结构、规则的松动,以及法制的开始建设(如“破产法”、“出版法”等的制定)、法治的初步萌芽(如基层选举)等等。我以为它们才是走向未来民主政治的客观力量、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我不相信凭几个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要求“领导阶层自律”就能建立法治。其实,从二十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曾不断引入和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法治观念(尽管不一定理解得非常准确),但根本无济于事。一百年来,文化变迁、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都试过了,但没有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大变动,民主、法治在中国还是建立不起来,各种宪法都是一纸空文。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林毓生先生的重点在于把今日中国创造性地“转化”到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规范标准中去。而我强调的则是通过“转化性创造”,即逐步改良的方式,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但不必全同于西方的形式、模态、规范,其中也包括法治体系。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同意(也有某些严重的保留)崔之元的观点,不赞成“制度拜物教”,即把西方既定的形式、模态、规范视为普遍适用、绝对神圣的标准而无条件地搬用。
——摘编自年9月26日思想潮推荐的《李泽厚、刘再复:法治的理想与现实》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jj/1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