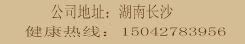和K分开旅行的第一天坐大巴到了索菲亚,刚到索菲亚就被自己定的廉价booking给骗了。付了钱,到了给的地址,敲开了门发现这的住户已经在这住了很多年,前台电话打不通,消息也不回复。原来用了真的外景照片和假的内景图,让人以为是个正经旅馆。第一次用booking被骗,心情荒诞。我到附近一家四星级酒店借卫生间,前台是一个叫娜塔利亚的女人,大概四十出头,金发厚唇,优雅沉稳,处事不惊,用面对孩子犯错的无奈眼神看着我。她说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折扣,一间房50欧一晚,我跟她道谢和婉拒。她帮我打电话报警,又给booking打电话帮我退钱,最终重新定了青旅。我坐在酒店外的咖啡座一直画画发泄,和朋友打电话,等到了入住的时间,拿回充电宝和娜塔莉亚告别。出发到青旅,然后睡了一整天。初到索菲亚觉得好萧索啊,首都没有首都的样子,建筑年久失修,墙皮剥落,到处都是二手店,很多无所事事的警察。人们走在街上提着大型外国超市如Lidl和billa的购物袋在街上没有目标地行走,生活被工业侵蚀着,愁眉不展,汗水蚀刻在褐色脸颊上,写着生活不易。穿过几条街,有很多零售店,让人觉得经济不景气,仿佛他们的钱只够买很多小玩意儿。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酒和糖一起卖的小店,和随处可见的赌场。整个城市都不尽人意,但奥斯曼时期建造的中央温泉却很温暖,在夏季冒着热气,所有路过的人都能在这接上一杯泉水,有人用塑料瓶把泉水装回家,流浪汉在这洗脚。我想象着冬季,再绝望的人和动物能触摸到天然的热水,也会觉得治愈。这大概是这座城市最平等的地方,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实用宝藏。我带着疲惫和伤感,大脑一片混乱,在土耳其餐馆吃饭。因为疫情不能去希腊,也不能去土耳其,下一步不知道去哪。老板Mahmut指着新闻说就在刚刚土耳其打开了边境,我豁然开朗。他问我来自哪,我说中国,他想学中文,邀请我每天来餐馆教他中文。我想或许这次我能去土耳其,就跟他交换当语伴。模式是我想知道什么,他就告诉我什么。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问他“我昨晚梦到你”怎么说。“Senirūyamdagōdrum.”在土耳其语里是“我在梦里看见你”。原来梦是一种视觉,视觉是一种形象,形象是欲望,欲望是执着,执着是自我催眠困境,是幻想,是梦,是桥梁。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依据直觉所做的事,是不是早就一遍遍在梦的反复体验里演算好了,以至于看似偶然的事发生得这么自然。经过一个月旅行,到达索菲亚的时候我已经什么也不想做,就观察着他的生活。他收留并教会很多人技能,包括没有工作的保加利亚人,想得到签证的土耳其人。在餐厅里可以看到他丰富的社会关系网,来店里的客人有土耳其银行工作的人,做移民生意,帮他们合法/非法移民到欧洲的人,送牛奶来的人,肉铺的人,送甜点来的人、收垃圾的人、土耳其律师、土耳其工人,他还收留了一个流浪老人,每天在店里和他们一起看球、吃饭、生活。人们来到这里,一起构建了这个时空,场域里是家的气氛。Mahmut请我吃早餐,有橄榄、黄瓜、番茄,他自己做的burek,里面是韭菜和奶酪,还有黄油蜂蜜土司。他从未停止运动,每一件事都会去参与和指导,时常和员工们开玩笑。中途有客人来就和他们打招呼互动,用尽他会的所有语言让客人感到亲切开心,一刻也没有停止散发生命。上课的时候,他给我介绍员工娜迪亚和奥斯曼,让我和他们聊天练土耳其语,也带我去朋友开的baklava点心铺。他问我想去参观索菲亚的什么地方,我说清真寺,他找到认识的人,打开门带我参观这座十六世纪建立的清真寺。世界被他的参与编织着,我在他的热情好客下被治愈了。他熟练六种语言,大多数来自面对面的交流,他给予他的技能,别人也教给他,他的世界简单直接,没有阻力。客人给他礼物,桃子、烤肉、点心,他给客人一些折扣和温暖的语言。他总是在得到之前就想给与,当你说想了解语言时,他已经把课程、茶点构想好了;当你在店里时,他已经想把其他店和朋友介绍给你;当你说想去土耳其旅行时,他已经想到帮你找当地认识的人照顾你了,他像一口温暖的泉水。交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从易到难,让人们容易理解。就像他介绍自己的城市,先说伊斯坦布尔,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则告诉我更详细的地名,位于伊堡和安卡拉之间的D?zce。这种小小的细节和关照充满着他的人生经验。他对文字不感兴趣,语言是他交流的热情。他不用熟知英文的拼写法和深刻的作家,只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书中理念不曾束缚他,他灵活得像章鱼穿梭在世界,细腻的感知到达文字无法到达的缝隙。年轻的Mahmut做过很多工作,其中一份是在格陵兰岛开采石油。他看到一座座冰山在海上浮动,冰不只是蓝色和白色,而是彩色的。我脑海里浮现被欧泊光晕糖纸包裹的一座座冰山,在奇异的晚霞下熠熠生辉。壮丽的景象漂浮在他的眼里,他下垂的眼角边泛出彩色的光。随后他坐船经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从西雅图到纽约,在美国呆了11年,在餐厅当厨师,也教和别人语言交换学会了英语。受家人挂念最终回家,但为了赚钱来离土耳其不远又是欧盟国家的保加利亚。餐厅里的电视一直播放着土耳其的频道,里面有葬礼发生。我们去了一家中国杂货店,无非是中国批发市场的商店样子,在保加利亚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需求。我们在厨具货架时不知道怎么聊到一个土耳其传统,Mahmut出生的时候,家人把木勺子换成金属勺子。家人的习惯因为新生命的到来而整体改变,生活被镀上金色的时间,仿佛蜂蜜色的阳光照进这个家庭。这样的仪式感令人感动,不管在哪里,他心里都有一个被珍视的意象。“有什么能帮助你吗?”长发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问。“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我说,像一个疲惫的旅客来到冬夜的旅店,像逃遁到与世隔绝的小木屋。接待员充满理解,甚至建议我办一张借书卡。“说不定你还会再回来呢。”他目光沉着,仿佛料定我会回来,带我领了房间和桌子的号码牌,把我送进众神遗留藏匿的神庙。图书馆和医院,治愈我疲倦、敏感、妄想的心。木质的桌子和典雅的地毯环绕着我,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祈祷者。奇异世界的城门正向我打开。古代的阿拉伯商人和犹太商人来到一座城市会带来新奇货物,我能为这里留下什么?他走过来问我应该把我的姓放在前面还是名,哪一种我比较喜欢。“哪一种都行。”来自我的粗糙回答,我又把这些问题当做工具而没有从中榨取乐趣。我为我冷漠而粗鲁的语言感到抱歉,语言应该像胸脯一样柔软,由点扩散到面,并且有过渡地带不让人感到尴尬。我忘记问他的名字,我压抑社交的欲望寻求安静,或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看着桌子上的编号,发现图书馆里所有的单数桌子都消失了,疫情带来一次减法,人们和事物从本应该的假设中消失着。去了在郊区依山而建的国博,感到压抑和抑郁,看着Mitras乘驾马车的金像,我暗示自己很多遍“黎明就要到来了”,几乎在祈祷,从我肺部挤压出空气去献祭。妈妈,没有好消息。爸爸,从不传达感情。今后的人生应该如何继续,缺少家庭的力量,我可能燃烧不了很久。想到色雷斯人在黎明到来的时候被希腊人同化了,我在博物馆默默地哭。在青旅遇到一对巴黎来的越南裔父子,我们用法语聊天。他们散发着对中国的热情,激动地告诉我,他们的祖先明清时来自洞庭湖。历史将我们连接,暗自饱含深意。我逐渐感受到人的可贵,他们的生活、灵活的生命和无可替代的当下,比历史、知识、文化都重要,打破着陈旧和腐朽的思想,因地因时而调整状态。适应是一种智慧,融入也是。我想我缺少很多智慧,高效的生活习惯扼杀着我,真正的我。我意识到这次旅行应该称为旅行自助餐,想到哪就到哪,旅行饕餮,吃到涨破大脑和消化系统。我得到的太多了,也太脆弱了,我的体系不足以生存。我破破旧旧,摇摇欲坠,身体没办法分解这么多养分和糖。我讨厌鲸吞的自己,失去味道,那些美好的信息失去了质量和质感。下次旅行我决定至少一个月都在同一个国家生活。从图书馆出来经过市中心,发现有人搭帐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城市奇观。坚硬的地砖不能插入地钉,帐篷随时可能被风掀起,这种柔弱的抗议示威方式打动了我。本来准备长时间不说话,但是没有抵抗住好奇心,走上去和他们聊天。这是抗议的第45天,市中心有三个据点和一个巨大的帐篷营,这几个地方堵住了市中心的马路,所以市中心几乎没有车辆。一个离国务院建筑只有十几米的主营,人们来这边聊社会生活问题、签字、请愿总理下台,马路对面是总统府;另一个帐篷在离国务院5米的地方,是残疾儿童的妈妈们搭的帐篷;另一个是学生团体,在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城市公园中间;还有就是从各个地方来这参加游行的散军。每天晚上8点,大家在主营,也就是国务院门口发言、倡议,大概持续30-60分钟,然后大家开始游行经过这个城市的中枢:议会、国家美术馆、主教堂、国家银行、图书馆、鹰桥来到大帐篷营,有乐队演奏和纪录片放映,夏天有人提供免费的冰沙。波利米尔是这次活动的领导人,温文尔雅,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从德国留学回来一直在律师协会工作,也为很多人无偿打官司。他每天都穿着polo衫,带着墨镜,取下墨镜后是一双疲惫、慈祥的眼睛。他的背大概因为长期伏案有些微驼,在人群中很低调。他声音不高,情绪平稳、不外露,但大家在他面前都变得温顺。他英语不太好,先后介绍给我了三个人,一个是说英语的律师露西,一个是中文翻译乔治以及一个英语好的导游。露西看上去有些憔悴,她声音沙哑,眼睛红红的。我从她的告诉我总理在位11年,政府腐败,从教育、医疗系统偷了很多钱。她的儿子是兽医学生,但是没有经费和条件练习,每年学费欧,大多教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她的工资大概也是每个月欧。如果没记错她有法律的硕士学位,但是在目前的社会没有关系很难有上升空间。知识分子在这生活极为不易。在位的总理是前总理的保镖,当过司机、运动员,但是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人们选他是因为觉得他品尝过底层的滋味,代表着底层人民的利益,但是政府上台后逐渐利用权力敛财,建立起贪污受贿的人际关系网。目前他们希望政府下台,通过总统组建临时政府,然后进行新的选举,让精英领导国家,组建人民代表和监察组织。乔治是中文商务翻译,商业也涉及到法律,所以他懂一部分法律,在法庭上为中国商人翻译过。他和我妈妈一个年纪,非常谦虚好学,眼里闪烁着人文的光,恒定的光源追求着真理和正义。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我们在一起说中文,我说到一些名词他不明白,就用本子记下。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跟着队伍游行,他在路边停下,用腿夹住他的公文包,掏出本子记下的第一个词是“精英流失”,我们聊着天不知不觉落到了队伍的尾巴。他告诉我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付出了很多代价,他们本来有核电站,但欧盟叫他们关闭核电站,从国外买电,居民的生活成本升高。如果在外企工作,待遇会比国营的公司好,但因为政府腐败,外企逐渐离开保加利亚,欧盟给保加利亚的拨款也到了总理那。他说检察院和内务司被总理买通了,执政期间修改法律,“鬼子写圣经”就是现在的局面,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对他的表达感到吃惊。中途一个小女孩和她的阿姨坐进帐篷,我和她们聊天,她妈妈是钢琴家、爸爸是歌剧演唱家,现在在当音乐老师,但是工资还是不够维持生活,以及对各种现状的不满,于是参加游行。很多家长来参加游行,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没事做的我会和伊万一起跟小孩们踢足球。帐篷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人,厨师、软件工程师、戏剧学生、美院教授、心理学家、银行工作人员、失业者,有时间就会来讨论,让我想到古希腊畅所欲言的广场。有人陆续送来食物和水,有人签字后留下一些钱,还有陌生人骑车来送给我一个东正教的护身符。克里奥帮我搭帐篷,用pvc管压住帐篷边缘,然后用砖头压住管子,同时教我一些奇怪的希腊语。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会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但因为地缘关系,希腊语几乎是保加利亚人的第二语言。他告诉我市中心这一块黄色的地砖是奥匈帝国时候在奥地利烧制的,送给一个亲王的礼物,在地砖的背面还能看到奥地利的城市名称。而索菲亚市中心建立在Serdika古城5米之上,是公元二世纪的文明,那时候已经有了先进的下水道系统和教堂。我躺在交叠的历史上面,感到非常魔幻,辉煌的历史和当代的痛苦相分离,坚不可摧的政府大楼和在风中摇曳的帐篷形成鲜明对比。今天图书馆没开门,我坐在图书馆的门口的长椅上怅然若失,读着书。有一种飞虫长得很像花瓣,黑色混着白色,一片一片地飘落在我头发上、肩上、腿上,小的是大的的分型,越大越复杂,越小越纯粹。一个背着破旧背包的老人来看书,见没开门,就在门前的小花园里摆弄玫瑰花。她一身黑裙,一头白发,在炽热的玫瑰丛中佝偻着腰,我不记得她本来就有点驼背还是因为玫瑰而倾身。一个俄罗斯人从背后绕过我,踩在水泥地上干枯脱水的蚯蚓上,问我有烟吗,很经典的俄罗斯式开场。随后他提到咖啡和性,让我怀疑这是黑话。他说我有个旅馆你感兴趣吗?我说不,请不要和我讲话。谁敢相信在被基里尔和格拉哥里的雕像守护的神圣土地前,有人在这谈论性和交易。大概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公园。之前搭车,司机说有10%的保加利亚女人成为妓女,我感到难过。如果一个绝望、走投无路的女孩坐在这个位置,她是否会答应,走向看不见的路。想到那些随处可见的赌场收割着底层生存者的最后一丝侥幸,廉价的工业甜食提供着他们一天的燃料和安慰。我意识到我在法国遇到的移民,背后的国家问题绝不简单。黎巴嫩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暴富和赤贫,满世界的黎巴嫩人不是有钱出来挥霍就是没钱出来工作救济,马赛的保加利亚建筑工人出来寻求活路,还有因为土耳其种族主义针对的库尔德人,也在这生活着,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在这生存几代了。法国好像成为一个国际庇护所,人们看到一线希望。“真正的城市为公民带来对自由的挚爱”,法国曾经满怀这样的愿景,或者说欧洲试图构建这样的城市,可惜在资本的冲击下,理想被一点点击碎,人们看到的是充满戾气、体无完肤,不再相信理想政体的社会。daskilelouch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fz/7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