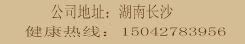蒋立波,又名陈家农,浙江嵊州人。曾与友人先后创办《麦粒》《白鸟诗报》《星期三》《越界》等民刊。曾获“柔刚诗歌奖”主奖()、“突围年度诗人奖”()、黎巴嫩NajiNaaman国际文学奖()等奖项。辑有诗集《折叠的月亮》()、《辅音钥匙》()、《帝国茶楼》()、《迷雾与索引》()。诗作被译成英、法、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文字。现居杭州远郊。
失联之诗
她把自己劫持到了哪里?
——王家新
一个词还在满天飞,尽管
它的骸骨早已坠落于泪水蓄积而成的
大海。鹤望兰高昂的头
像一部失灵的雷达绝望于
白玉兰的空管塔,只有钟表还在不停地
嘀咕:你这海鸥的登机牌现在
葬身何处?那些漂浮的碎片
仍在努力拼凑一册《解体概要》
因为每一次写作,都是对最终那个
伟大遗嘱的无限接近,或者背叛
仿佛大海里还藏着另一个秘密的大海
像词的公墓,寄存你遗落的发卡
我看见一把木梳骑着你的黑发
分开涟漪,向一个事实飞奔
而你已经失联。你关闭了全身的应答系统
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
你是你自己的劫持者,你就是那谜一般的
语法的创建者,你就是你的牢房
据可靠消息:天堂里的纸飞机起飞后
至少曾经有过“消失的一小时”
然后是漫长的沉默,一道幽深的海峡
终于对道德的此岸和彼岸作出区分
沿着未知抛过来的绳索,人类的泪水还在
向更高处的悲悯攀登。但我依然找不到盐粒腌制的
信仰,还有那本被无神论者冒用的护照
这意味着辩证法的俱乐部开始解体
这意味着大海太狭隘,理解不了
一枚针过于辽阔的苦闷
祈祷词太咸,合唱团里的空难纠正着
一只军舰鸟晕眩的时刻表
这意味着美学的血库开始告急:
一个失踪的词,把自己劫持到了哪里?
为黄公望隐居地的石鸡而作
(赠姚月,兼致永波、苏波)
一路上,总是有石鸡追随我们。
它们不屑于与青蛙为伍,不屑于
在庸常的田畴里,为农药喂养的水稻献唱。
鸣声铿锵、凛冽,森森然有金石之韵。
它们像是刚刚从黄子久的山居图里跃出,
还带着筲箕里漏出的米粒的清香。
总是有一种更大的矛盾,石缝里
隐逸与挣脱的持久的对峙;
总有一种复数的厌倦,为鲜甜的星光所孕育。
减速的激情,为随身携带的庙堂减去
一个多出来的观音;年轻的道士
在用旧的山川和烟岚里探测万物的回声。
农家乐的长廊下,它们还在你朗诵的童谣中
唱和或争辩,像是有一把幽微的锉刀,
锯开蛙皮下沉睡的道观。
而晦涩不是它们的错,正如唯物的卷尺
丈量不出现实褶皱里那隐秘的声带。
德语区里,格林拜恩与汉斯,拉出一条对角线。
菜谱里的细雨春山刚刚从酣睡中醒来。亚热带植物的根系,还没有吮吸到一孔确信的泉眼。出于虚妄,一棵樟树披上了豹皮,但对于一身斑斓的临摹,似乎仍然逊色于盘旋而过的麝凤蝶。假道现代性,人工水池的唱片,开始重播石鸡去年录制好的鸣叫。说起来可惜,晚餐你们终于还是没吃到毛笋,端上餐桌的,是另一种不知名的野山笋,纤细如一根根刺破寂静的针,此时,却被用于对寂静的缝补。细雨没有写进菜谱,但不知不觉中
它像一种额外的款待,在香椿炒蛋和凉拌蕨菜之间到来。
“而这些山是一种剩余,等待着枯干。
风格随暮年的积雪慢慢消融,直到只剩下嶙峋本身。”夜色中,白炽灯的钨丝嗞嗞作响,像是对时间谨慎的抵制,或者一种小声的忠告,提示我们诗行所承受的电阻。
与王家新在洞头岛
昆虫研究
(给张壬)
你拍下这么多昆虫,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也认不出它们的样子,更不知道
它们所从属的目,科,种,属。
但我应该在哪里见过它们,听过它们演奏的音乐,
那神秘的音叉,琴键,簧片,身体的发声学。
我所缺失的恰恰都被它们所拥有,
我不可能借到它们的翅膀、触角、口器、伪足,
它们的管状心脏、梯形神经和越界的器官、拟态的涂料。
我只拥有莫名的敌意与一腔无用的怒火,
像一盘西瓜上空低低盘旋的苍蝇,
将一颗碧绿的头颅奋力投掷,
但我不可能借到它的复眼,以便反复计算
向一首意外的诗发起突袭的距离。
我拍死过的蚊子莫非已多于冒死投奔的文字?
这样的提问并不夸张,因为只有绝望
约略相同,像诗句的刺吸式细针日夜抽取
却在一瞬间将一袋救命的血浆归还。
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一次次地死里逃生,
窃喜于第二天醒来仍有一碗稀粥,
就着一碟花生米,和刺鼻的雾霾一起吞吃。
偶尔羡慕金龟的甲胄,螳螂的大刀,
等待一个唐吉诃德借我的身体还魂。
更多时候你或许会赞同,有必要在歌剧院的乐谱上
嵌入蟋蟀的音键,在螽斯的电报机里
抢救出银河系发来的电波。
——天牛。田鳖。蝼蛄。窃蠹。
——姬蜂。寄蝇。石蛾。龟蝽。
你熟悉它们如同你诗行里的每一个标点
都由它们构成,甚至你每一天的晚安
都模仿了它们的口型和腹语。
尽管失踪每天都在这个国度发生,再见
或许就是两颗行星之间的永不再见。
每天,胡蜂举着螫针,蜻蜓替我们携带细长的塔身,
在黏稠的气流中超低空飞行,而蜉蝣
忽然生,忽然死,用一日叫板我们冗长的一生。
你日复一日拍摄它们,是否是要告诉我们
晦暗的时刻还有瓢虫的星辰闪耀,屎壳郎寄身的粪堆里
也有一个微观的宇宙在翻身,并且从那里
齐刷刷探出一张张迷惘而严肃的脸。
衣鱼
衣鱼,这好听的名字,它的发音听起来像是
抑郁,异域,呓语?其实它就是书蠹,
一种寄身于书柜的缨尾目昆虫。
它吞吃浆糊里的葡聚糖、书籍装订线、纸张、相片
毛发、泥土、亚麻布、丝绸、人造纤维。
我说,这一定是它的笔名,吃掉了这么多字,
它应该也会写诗。它并不是鱼,尽管
它畅泳于词语的惊涛骇浪,一本书中埋伏的
暗礁或漩涡,而最吸引它的,无疑
是一首诗没有写出的部分,比如莲塘深处
一声不吭的藕、习惯从不表态的淤泥。
它既吃“晦暗的鱼鳞”,也吃嘹亮的蛙鸣,偶尔
在褒义词与贬义词之间费尽踌躇,
在悲痛的词与狂喜的词之间左右摇摆。但极少
咬到一根履带,一截墓碑,因为在它之前
这些沉默的早词已被更锋利的牙齿挖去。
其实它并不需要一口池塘,更不需要一座大海,
喂养它的恰恰是干旱,那“满纸荒唐言”,或者干脆
就是一纸空文。在历史的迷雾中,
双关,反讽,虚拟,口吃的修辞穷尽之处,
衣鱼沾着满嘴的胶水和我们说话:“此处删去……”
西湖夜游
晚饭后来到西湖边,我们依然一如往常
慢慢地走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或许那些更动人的言辞已被永久封存,
像炫目的冰淇淋,需要到下一个夏天才能融化。
或许踩过落叶的瞬间,你曾有过短暂的迟疑,
那无声的变形接近于一次完美的折叠。
一个不为人知的锐角,在桂花灵敏的嗅觉里惊醒,
水洼中霓虹的倒影扶起一座老迈的剧场。
湖水终于冷了下来,黑暗中我看不清
远远近近的荷花,一柄正在缓缓收拢的雨伞,
旋出一颗被墨绿吸管反复饮用的雨滴。
而饮用也是引用,伞柄卷起的弯钩垂钓
荷叶卷边的记忆。你指给我看一盏路灯的灯罩下
奔趋的蛾子,这盲目的舞蹈服从于一种
集体的晕眩,像忠实的灰烬把光束一次次擦拭,
以便分娩出一道陌生的光源,为新的失败加冕。
取景框里,远处的塔变得模糊,但塔尖
在努力挣脱出来,像蜻蜓身体里一截失效的电池
仍在制造一场余震,将一枚颤栗的尾音缓存。
当游船从对岸回来,一支畅泳的桨
带回水草和鱼鳞的叮咛。更多的涟漪还在涌来,
穿过鲜嫩的莲藕中密布的更完整的桥孔。
某些时候,你分明已远远走在我前面,
但始终有一根丝线在绷紧,相切于一个隐匿的湖。
年9月5日,与女儿游西湖
与阿九在诸暨石佛小院
皱缩的石榴
你几乎已经无法辨认出它,搁在书桌上
像一只粗糙的陶罐,只是你即使用力摇晃,
也不会再有水声传来。你想起埃利蒂斯写过的
疯狂的石榴,那饱满的籽粒,曾经胀裂
如一个微型宇宙,听命于一种精密的机械。
但霍金说过,宇宙也在不断萎缩,那向内的塌陷。
你没有注意到它的枯干和变化。那缓慢地
交出自己的过程。交出水分。交出汁液。
有没有交出灵魂?无人知晓。反正你仍然可以
凝视它,像凝视晚年的奥登,那地图一般
驳杂的地貌。直到只剩下枯干本身。或许
事物负有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让自己不断变丑,
在一种反义中重获自己,让喧哗的寓意归于
本体的安静。它驱使自己走向高度的抽象,
或者自己的对立面:轻,轻到无法称量;
甜,甜到舌尖倏然缩回字面。这时间的果实,
衰老的博物馆,以完整的闭合拒绝你。
只有当你把它放到耳朵边,像一名间谍
窃听词语内部的风暴,那簇拥的星群
仿佛又开始在众多的房间踱步,而你仍然
无法窥探一个守口如瓶的宇宙。半径
在公式里沉睡,你,被一只沉默的石榴掰开。
词源学三口井竟然还在,一口正方形,两口三角形,我最初所接受的几何学:从这里出发,我和世界构成了无数个直角、锐角、钝角。而如今面对被遗弃的荒凉,所有的公式都已宣告失效。中年的杜甫?我不可能想像他的形象,或许只有他内心蔓延的荒草能够替我丈量遗址的面积。吹过我耳廓的秋风,一定也计算过他两鬓的白发,那浸入草木的霜,遍地的瓦砾上,中年的积雪。故乡是最大的虚妄,因为叫得出我乳名的人都已经不在,我想拥抱的仇人也已在泥土深处长眠。他们不可能再醒来,沉重的墓石背后,缄默的嘴唇不会有任何一个词需要向我吐露。但当我站在八十岁的阿叔和阿婶中间跟他们合影,我几乎听到了头顶三只竹篮里储藏的土豆种子那幼芽拱动的声音,我甚至想像他们拄着的拐杖也在抽出嫩枝。这么多年我远走他乡,而我不可能背走这三口井。记忆总是热衷于不断修改自己,只有三口井忠实于自己的位置,它们分别被用于饮用、洗菜、洗衣,很多年里都相安无事。井水不犯井水,蛇和井绳彼此仿写来自命运的紧张与敌意。乌鸦和喜鹊,在同一根树枝上
发表相反的意见。仿佛母亲的水桶还在依次碰响井沿,蛙鸣,青苔,姓氏,晃动的冰块与星辰。我已经习惯不断地删除,习惯与世界的平行关系,但我保留了凛冽与暗涌的天性,一个隐秘的锐角,或者说我与我之间固执的对质和争吵。泉孔在看不见的地方教育着我,如同旧雪
在“记忆的阴面”⑴冰镇我的童年,一种不被讲授的
词源学,需要从枯枝那里借到一根仁慈的教鞭。
⑴.“记忆的阴面”借用自耿占春
纪念张爱玲
(与桑克同题)
前些日子刚去过胡村,白墙粉刷如新
在别人的故居里
你那张经典的照片看上去像是陪绑
玻璃镜框后面,目光中那份淡淡的嘲讽依旧
双手叉腰,像一副傲慢的圆规
但并不是为了把漫长的生命
画成一个圆圈,尽管你写的最后一本书
《小团圆》有三个版本
分属于自传、散文和小说
像无法执行的遗嘱被三种文体瓜分
明天就是中秋,月亮在无限地趋向圆满
它拥有的版本无疑远远不止三个
但不可否认孤独是你在人世唯一的半径
话柄就是斧柄,模糊的环形山
像失血的静脉伸向一个传奇
你始终是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咖啡杯上口红的唇印像一对借来的括弧
而除了荒凉,你并无更多的生平需要加注
旗袍下起伏梦中的旧山水
那被裹紧的身世,允许有隐秘的分岔
为了跟更多的跳蚤搏斗
你的后半生都在不停地搬家
生活就是误解,爱就是走向深渊
公寓的镜子只提供悲剧的副本
“再来一份狮子头,再来一碗鸡汁羹”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新时代少女
像未及卸去浓妆的群众演员向我们走来
在你曾经的赤地,秧歌已扭成热烈的广场舞
年9月30日
年10月1日修订
与李龙炳和高春林在富阳东梓关
听力中的重音
我的听力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
许多次和朋友交谈,我都要侧过耳朵
才能把听力中的重音加以辨认。
即使惊雷,当它抵达我的耳膜,
也可能只约等于蚊蝇的嗡鸣。
但也有例外,每当夜深人静,
我无数次从睡梦中醒来,
然后,长久地失眠,就像一个囚犯
被流放到一颗荒凉的星球上
那种漂浮,抛离,无所依傍的茫然。
而正是这样的时刻,我会不由自主地
被若干种细微的声音所吸引。
我知道,那是油亮的蟑螂
在高大的书架上疾走,小乌龟
在塑料盒子的内壁上一次次
攀爬,又一次次,重重地跌落。
通过丝状触须小心的探测,和脚趾
奋力的抓取,书页间沉默的部分,
黑暗中那些无法翻译的语种
得以被触及,词的交媾和繁殖
也在反复的摩擦中被照亮。
餐桌上的知了
知了在餐盘里沉默着,这些刚刚从沸腾的油锅
捞出来的幼虫,来不及发育的小尸体
油腻的菜谱里嵌入的十字裂纹
金黄,酥脆,以同一种待飞的姿势
接受贫乏味蕾的诱捕和训诫
焦黑的声带不可辨听,舌头席卷
地下漫长的变声期之后郊区的冷僻口感
元音与辅音似乎已达成可怕的默契
一种美学的独裁,小心剔除牙缝里残留的国家大事
用退化的味觉兑换童年持久的幻听
这几乎已接近于一种纠正
像少年隆起的喉结,为保护名录中的鲨鱼鸣冤
知了深知我们的饥饿,一件滚烫的乐器
深知簧片的干渴。当我们的牙齿
咬紧那鲜美的肉,我担心
一只死去的知了将在一刹那活过来
我将用知了的口型,发出曾被消音的第一声鸣叫
而窗外的树干上,更多的同伴正埋首于狂饮
乡居隔离指南(五)
晚饭后散步,往往已经天黑,只能见到两边群山
巨兽般蹲伏,默不作声,甚至山冈上的信号塔
也已不再接受信号,包括那些蜂拥而来的,
关于死亡与春天的谣言。溪水匆忙,在黑暗中
听起来比现实抽过来的耳光更响亮。乡村公路上,
蝙蝠在避让,车辙撤回确信的里程,犬吠
拓印空旷里潜伏的危险。路边几块墓碑兀立,
我看不清上面的文字,但我知道不可能有墓志铭,
甚至省略了必要的籍贯、生卒年和立碑者名字,
这冷僻的文体把我们隔离于悼念者的行列,
似乎凡夫俗子只需要草木的铭记。但我仍然提醒自己
放慢脚步,压低声音,因为真正的训诫来自潦草的藤蔓
和被冷落的幽灵。而往往是这样的时刻,是他——
九岁的男孩,在一架飞机远去之后,准确地辨认出
头顶的北斗七星,这晦暗星系中夺目的存在。
也正是这样的时刻,迷途的信号塔被他从雾中捕捉,
一只干渴的木勺弯下腰来,俯饮到我身边这条无名的小溪。
蒋立波新诗集:《迷雾与索引》(),北岳文艺出版社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huochonga.com/lnfz/5764.html